
12月11日夜,贝尔拉格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院长(director)Vedran Mimica,以“贝尔拉格如何做教育?”为题,于有方502带来讲座。讲座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贝尔拉格建筑学硕士朱亦民主持并翻译,翻新后的有方502也迎来了一场华南片区贝尔拉格学子的重聚。




Vedran Mimica出生于克罗地亚,于代尔夫特求学时受教于贝尔拉格创始人赫茨伯格并为忘年交,在贝尔拉格创立初期,便受赫茨伯格委托参与学校日常事务、教学管理。Vedran可谓是贝尔拉格往事“从头至尾的见证人”,被弗兰姆普敦称作“贝尔拉格的精神领袖”;然而在讲座前与有方的交流中他表示,“今晚不应是我一人对贝尔拉格的回顾。你将直接听到赫茨伯格、库哈斯、扎哈、齐埃拉·保罗、雅克·赫尔佐格、让·努维尔等人的声音——这,才是真正的贝尔拉格”。
贝尔拉格在作为独立学院存在的22年历史中,与当代众多重要建筑师、理论家均有着密切的联系。讲座伊始Vedran便定下规则,“亦民,每次我讲完之后,你的翻译不要超过15秒”——在与包赞巴克类似的“争分夺秒”后,Vedran以滚石乐队Sympathy For The Devil中一句“pleased to meet you”,揭开了这场贝尔拉格往事的序幕。


贝尔拉格建立于1989年末,2012年合并入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波谱与安那其主义对体制的反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文化动荡、哈贝马斯等智识分子对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反思,无疑都是贝尔拉格成立的基因。
而在作为独立学院运作的22年中,贝尔拉格首先是一个论坛和平台,当代绝大多数重要的建筑师、学者都于此留下过自己的印迹,在某一段时间发生过影响。
贝尔拉格由荷兰著名结构主义建筑师赫茨伯格创办。在今日的建筑史课本中,1960、70年代有两个无法略过的房子:阿培尔顿的中央管理保险公司总部大楼(赫茨伯格设计)和阿姆斯特丹孤儿院(范·艾克设计)。这是荷兰结构主义学派的两个代表作,而1980年代末,当孤儿院面临拆迁,赫茨伯格发起了一场保护运动,同时希望创办一个体制外的建筑学校,就在孤儿院的空间中办学。这就是贝尔拉格学院的开端。



贝尔拉格创办人赫茨伯格,是Vedran在代尔夫特求学期间的教授。1988年,赫茨伯格与Vedran于斯普利特(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举办国际设计研讨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与导师一同,参与为期5天的工作坊。这个国际设计学生的交流聚会,启发了贝尔拉格学院后来的创建。

受赫茨伯格邀请,Vedran在1990年、贝尔拉格成立伊始,就进入学校参与日常事务和教学管理。Vedran接触了非常多的曾在贝尔拉格教书、访问的建筑师、学者,也与学生有直接、密切的交流——他是贝尔拉格22年历史“从头至尾的见证人”,是学院最后一任院长(Director),被弗兰姆普敦称为“贝尔拉格的精神领袖”。


讲座中,第一位以视频回顾的形式被Vedran“请来现场”的,是贝尔拉格创始人赫茨伯格。

在自己的最后一节课堂上,赫茨伯格站在他最喜爱的一幅画作:梵高《吃土豆的人》前这样说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画。它并不美丽,相反,画面上的人们有着痛苦。然而这正是世界现在的状态,也因此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和处理的现实。”
对于有着人本情怀的结构主义者赫茨伯格而言,建筑师不应为形式(shape)而设计,而是应将内容(content)、将人类生活的场景作为设计的基本条件。这一理念也贯彻于他对贝尔拉格学生的教育中,“不要做和我一样的建筑,而要去理解人类的基本处境。”
赫茨伯格时期的贝尔拉格,向往的是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倡导的寓教于乐的学园,而库哈斯却称此为“蒙台梭利暴政”。库哈斯认为赫茨伯格的理念不够现代,就仿佛荷兰还处在一个农业社会——“in principle isn’t all Hertzberger ever talks about, that you need a special brick to put the milk bottles on at the front door? ”
然而尽管两人的思考可以说是完全对立,但库哈斯在批评之后,却被赫茨伯格邀请加入了贝尔拉格的教学。在荷兰文化里有一种基本的容忍区别的价值观,“Talk with the monster”是荷兰传统。


贝尔拉格此时期最重要的交锋,发生在库哈斯与弗兰姆普敦之间。

在贝尔拉格成立初期,赫茨伯格为弥补当时学生在思想性理论层面的欠缺,在1992年请来好友弗兰姆普敦组织理论课教学。而库哈斯的观点与弗兰姆普敦的完全不一样,他认为城市不是由建筑师的伟大想法而创造,也不是追随在设计宣言之后被建造出来——库哈斯认为,深刻影响城市的,是经济与资本等其他力量。所以,在建筑师的想法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空白;而贝尔拉格的实践则应是通过对新思想的探讨,对这空白进行填补。
另一位对贝尔拉格有重要影响与思想贡献的建筑师,是扎哈·哈迪德。而通过1993年赫茨伯格在扎哈讲座前对她的介绍视频,Vedran回顾了贝尔拉格选择、邀请建筑师与学者的准则:“如果今日有人谈论建筑学的危机,那么危机肯定不是在技术层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创造出远超我们想象的东西。今日我们面对的危机在于人们的接受能力,在文化中,它也日益将世界分割为不同的阵营。一直有人问我,什么是贝尔拉格发出教学邀请的标准?毫无疑问,我们就是想邀请乐观主义者,邀请那些一直在探索空间可能性的人。就像扎哈。”
也许是因为来自贝尔拉格的邀请,让1993年时的扎哈太过意外,她没有回复赫茨伯格的信函。于是赫茨伯格让Vedran前往伦敦,并最终说服扎哈来到贝尔拉格,展示了她的第一个作品:在维特拉园区的消防站。


赫茨伯格定下贝尔拉格院长每五年一任的规矩,并在1995年将学校交给了当时与赫尔佐格及德梅隆、齐普菲尔德等齐名的荷兰建筑师,维尔·阿雷兹(Wiel Arets)。

继任者带来的是贝尔拉格学术谱系的转变。赫茨伯格是“30后”,是战后一代建筑师培养出的学生,他信奉的是反形式、无政府主义,交往密切的是“十次小组”(Team X)的范·艾克等人。而维尔·阿雷兹是在1970年代、“纽约五人组”如日中天时接受教育,跟美国建筑师关系密切。他的继任,在贝尔拉格和美国建筑界之间架起了桥梁,也进一步使李伯斯金、西扎、扎哈、汤姆·梅恩、哈尼·拉希德、斯坦·爱伦、格雷格·林、Liz Diller、Winy Maas等建筑师加入了贝尔拉格的教学阵营——今日回看,这样辉煌的教学名单,可能已不易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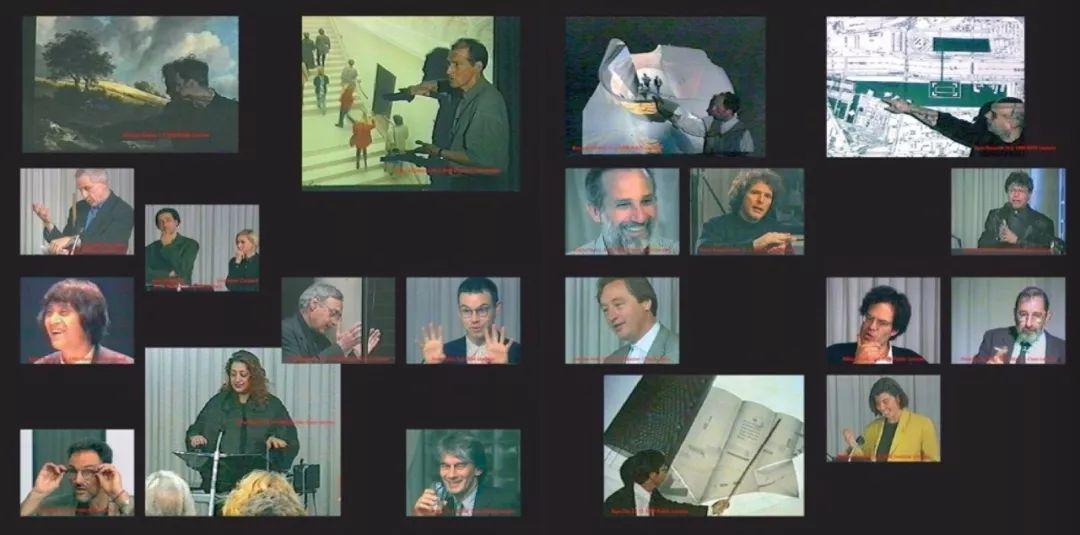
2002年,西班牙建筑师、横滨码头的设计者齐埃拉·保罗(Alejandro Zaera Polo),成为贝尔拉格第三任院长。此时凡·艾克已去世,而曾被他明令禁止踏入贝尔拉格大门的彼得·艾森曼,也终在新任院长的邀请下到访了贝尔拉格。

齐埃拉·保罗认为,建筑教育必须能突破既成的框架,必须进一步思考“我们还能贡献什么”。所以当时他跟Vedran说,“接下来我们只邀请未满四十岁,能在目前的建筑教育体系外引入新的现实、革新建筑领域的人来贝尔拉格讲学”。推动世界的改变,是保罗的基本观点。
然而当保罗邀请的其中一位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谈及建筑师存在的意义,被突出强调的仍然是建筑从情感上触动人们的能力。就像孩子还是可以为大教堂所震撼,赫尔佐格依然相信建筑学的物质性,相信其情感的力量——“只要建筑动人的能力仍然存在,建筑师就仍可以’生存’”。与激进于建筑革新的保罗相比,赫尔佐格的命题无疑更为传统,贝尔拉格也依旧是那个各种声音都会出现的地方。
讲座尾声,是Vedran对自己作为贝尔拉格最后一任院长的实践回顾,城市是此阶段的核心议题。而在持续20年后,贝尔拉格师生建筑探讨的批判性也愈益强烈。
在贝尔拉格的最后五年,Vedran依然继续着和库哈斯的密切合作。而库哈斯此阶段曾于贝尔拉格讨论的一个有趣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自己的身份:明星建筑师。Vedran笑说,”库哈斯可能不会允许我公开他的这个观点,但这确实是他当时的思考:‘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持续的地标生产中,我们得到了巨大的关注和曝光,但愿意严肃地看待我们的人却越来越少……在明星建筑师受到大量关注、取得了社会的认可后,却可能因为不再参与住宅等社会性项目,反而与社会相脱离。’”

某种意义上,这次讲座并不是一场知识性的、对于贝尔拉格的“讲解”。在两位”贝尔拉格当事人“——Vedran与朱亦民——陈述或翻译阐释的字里行间,讲座触及的是对这重要机构或许朦胧感性,但无疑立体真实的气质。
讲座尾声,Vedran提及贝尔拉格在最后一个阶段,试图跨越“mapping”与“投射”(projective),找寻出口的努力;而就如朱亦民最后的总结,“Vedran一直在通过一些具体的发言和观点,来孵化这样一个线索:贝尔拉格始终在试图讨论最前沿、根本、关键的问题,没有完全陷入技术官僚的层面。不把教育当作纯粹工具性、仅解决自己专业问题的存在,可能是理解贝尔拉格时始终的背景。这样一个基本价值观,我认为22年都没有改变过;对于社会、城市、建筑的关联性,贝尔拉格一直在发出自己的疑问。”



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欢迎转发,禁止以有方编辑版本转载。
上一篇:建筑地图59 | 金泽:日本隐藏的宝地
下一篇:JKMM创始人Teemu Kurkela:幸福的建筑配方|有方讲座47场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