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爱万物之始。
万物皆始于将发未发之际。
我深信,事物一经发动,
它的方向即已固定,
无论往昔、今日与将来。
——路易斯·康

本文首发于金秋野建筑工作室,转载已获授权。
文 | 温迪·雷瑟Wendy Lesser
译 | 金秋野,北京建筑大学教授
他的同事们都觉得他的作品非同凡响,他们也都毫不犹豫地认同他是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建筑师之一。在这个行当里,尽管有那么多的建筑流派和风格,人们却普遍尊敬他的成就。与漫长的一生相比,他的作品不算太多,但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带有浓浓的个人烙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着人们的感官。
这份天才理应遭人妒忌,实际上却鲜有如此。原因大概在于,他在自我经营方面极其笨拙,事务所的财务一塌糊涂,令人不忍视其为竞争对手。又也许,是他柔和的性格让人们放下了戒备。他的童年时代一贫如洗,求学生涯乏善可陈,外形更是毫无魅力可言。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别人难以从他的性格中感受到威胁。即使是在最亲密的人们中间,大家都了解他有多么了不起,他给人的感觉依然是和蔼可亲、息事宁人,甚至带一点自嘲。

路易斯·康是个热心、让人着迷的人,他的学生爱他,同事爱他,朋友爱他,他的魅力,无论对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别无二致。但他也是个有秘密的人,真实的内心躲在重重遮罩后面。第一重遮罩是物质性的,就是他脸上的永久性疤痕,源于童年时期的一次意外;第二重遮罩是他保守的私人生活——与艾瑟尔·康(Esther Kahn)长达44年的婚姻,她是他大女儿的妈妈,也是他在费城社交场合的公开伴侣。这份婚姻遮盖了康与另外两位女性的罗曼蒂克故事,她们是安·婷(Anne Tyng)和哈莉娅特·派蒂森(Harriet Pattison),两人都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再有一层遮罩,就是他的姓氏。那根本就不是他的本姓,是他父亲省事给他取的一个绰号,后来在移民美国的时候,全家都跟着姓了Kahn。路易斯在爱沙尼亚的时候,本名莱瑟-伊泽·舒慕伊罗斯基(Leiser-Itze Schmulowsky),到了美国变成路易斯·爱撒多尔·康(Louis Isadore Kahn),本意并非为了摆脱犹太身份,而是从东欧低种姓犹太家族摇身一变,成为备受尊崇、声望卓著的德国裔高种姓犹太家族。而犹太身份本身,对康来说无异于另一重遮罩,让他得以面对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的费城主流社会,更不用说典型新教徒主宰的建筑世界。但对他本人而言,信仰则没有什么要紧。跟教堂和清真寺相比,他的确接受了更多的犹太会堂的设计邀请;但最终却只有一座清真寺(达卡议会大厦中的礼拜堂)和一座教堂(罗切斯特的唯一神教教堂)成为经典;所有的犹太会堂设计都停留在纸面上。“我的信仰太过强烈,以至于不能随便相信任何东西”,有一次他对朋友说。当时一个重要的费城犹太会堂委托刚刚胎死腹中,此前经历了数年的艰难推进和无数的冲突,有些发生在他和教众之间,有些单纯是教众间的争吵。
或许他想说的是,他唯一的信仰就是建筑学。每一位认识他的人,都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他的妻子、情人,他的三个孩子:苏·安(Sue Ann)、亚历桑德拉(Alexandra)和那撒尼尔(Nathaniel)或早或晚都意识到他的所爱就是自己的作品。他的助手们经常提起他巨大的专业热情,(怀着幸灾乐祸和失望的心情)不断强调他只在乎建筑的艺术方面,对经营一窍不通。即使是那些客户,因为他迟迟不交方案而暴跳如雷,也能理解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强迫症晚期,而不是因为倔强或判断失误。

爸爸希望他成为一个画家,妈妈则希望他成为音乐家。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父母双亲就在他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天分,而终其一生,康也努力去发展自己的天分。到一定年龄,他的父母终于意识到,康一旦发现了建筑学,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说康对这条路毫无悔意是不准确的,因为即便是谈到“悔意”便意味着有其他替代路线可走,而对康来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他生而注定成为建筑师,他自信、自觉、自愿如此,这深埋在他思想的核心部分。“你对砖说:‘砖你想成什么’?”在一次充满了格言警句的谈话中,康这样说道。“砖对你说,‘我喜欢拱’。如果你对砖说,‘拱很贵,我可以做个混凝土过梁来跨过洞口。砖你觉得如何?’砖说,‘我喜欢拱’。”对康来说,与材料天然的属性对抗是毫无意义的——包括跟自己的本性。
这并不是说康是个自我为中心的控制狂或权力欲爆棚的疯狂建筑师。这种个性的男主角建筑师在小说和戏剧里不乏先例,像易卜生笔下的哈尔瓦德·索尼斯(Halvard Solness),以及安·兰德笔下的霍华德·罗克(Howard Roark)。面对这些想象出来的建筑师角色,作家们或者全盘否定之(像易卜生那样神经兮兮),或者满怀妒意地拥抱之(像安·兰德那样笨手笨脚),不管哪样,建筑师都像是个核心人物,在自己的世界里呼风唤雨。他不仅决定人们的生活环境,甚至也摆布环境中的人。女人对他的魅力无可抗拒,他把她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对所有人的命运予取予夺,包括他自己也包括别人,不管他遇到的是鲜花还是陷阱,作者和他本人都认定他是自己命运的导航者。
这种对建筑师形象的刻画,可能并不适于路易斯·康。(很可能也不符合任何真实的建筑师,甚至奥斯曼男爵和阿尔伯特·斯皮尔也不符合:现实,哪怕是最离经叛道的一种,也跟作家的狂野想象有相当距离。)如果康是个自大狂,那也应属于极其特殊的品种。他是个宽宏大量的自大狂,希望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得到莫大的生命的快乐。他是个有同理心的自大狂,他的工作高度依赖合作,且能让合作者感受到各自的贡献,哪怕只是关于一个视觉元素或一种特定建筑材料的知识。他是个诲人不倦的自大狂,鼓舞学生们开拓自己的事业。作为一个自大狂,他能洞察并了解任何有生之物的自我意识,甚至一些无生命的事物——比如砖——也有其自我成就的愿望。或许,以常识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即便有,也是以一个孩子的方式。但他显然明白自己的价值,他信赖自己的直觉,以他特立独行的方式,表现出一种造化无情。这些特质让他能够直面生命对创造性的巨大阻挠,完成属于个人的建筑奇迹。

建筑师是一类特殊的艺术家。跟画家和音乐家相比,他与最终的作品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这个作品的完成过程、最终展现出来的样子,甚至这个作品是否真的会盖出来,都受制于大量不可控的因素。钱是其中之一;业主的品味也难以捉摸。本地的气候条件、建筑法规、材料获取的途径,都或多或少地发生影响。甚至历史、政治和宗教信仰,这些建筑师并不擅长或并不熟悉的因素都会对方案发生潜在的影响,项目越大,这种情形发生的几率越高。
所有的艺术似乎都包含“机缘”的因素,建筑尤其如此。像一位电影制片人或舞台剧导演,建筑师必须依赖很多他人来实现自己的作品。这些人不仅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要对建筑师脑海中看到的图景怀有亲切感,至少不是一无所知。一座建筑的建造过程中,有一万种可能偏离初始意图,只有一条路通往正确的方向,而其人偏偏能让事情沿正确的轨道运行,每思及此,不得不赞叹建筑师成功的价值。
对包括康在内的很多建筑师来说,一边是脑海中丰富的想象,一边是不断涌现出来的麻烦,如何协调二者间的关系,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基本问题。康不是一位离群索居的天才——靠不断打磨自己的观念以臻于纯粹,然后让它们分毫无差地建造出来。他毋宁是个高超的合作者,能鼓舞人们全力以赴地工作,让这份热情感染业主,成为他的同谋。无论是检视自己的观念还是别人的想法,康都一直保持一种无情的节奏,判断、选择、修补、放弃,直到达成所愿。面对业主的请求——常常是出于经济考虑而要求缩减规模、至少是降低造价——他会不断返回绘图板,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他不是舞台上的女主角;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个实事求是的建造者。与此同时,他也绝不是个耳根子软、好说话的人,而且没人能够强迫他在自己不认同的方案图纸上签字,这一点越到后来越是如此。
但这种特立独行的愿望、这种独一无二的介入方式,并没有演变为肉眼可见的“风格”。如果你看见一个罗伯特·文丘里或弗兰克·盖里的建筑,哪怕你之前从不知道设计师是哪位,都能轻易地认出来这是文丘里或盖里的作品,因为它们的造型本身就带着设计师的标签:那些非对称的、像面孔一样的后现代立面,或钛合金的反光表面。但路易斯·康的经典作品却与之相反,并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相似之处,而且外观上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似乎很难从外观上认出一栋建筑的设计师是康。只有当你进入内部,整体的空间感受和漫游的经验才让你恍然大悟——这是一座路易斯·康的作品。你会同时感觉到欢乐与慰藉,一种被空间密切包围的幸福感,同时精神被引领,进入崇高纯洁的领域——这大概就是康希望在建筑中传达的、也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精神氛围。但并不是每个作品都是如此:康也有失败的时候,就像其他艺术家一样。而当正确的氛围出现得足够频繁,就足以使这位建筑师脱颖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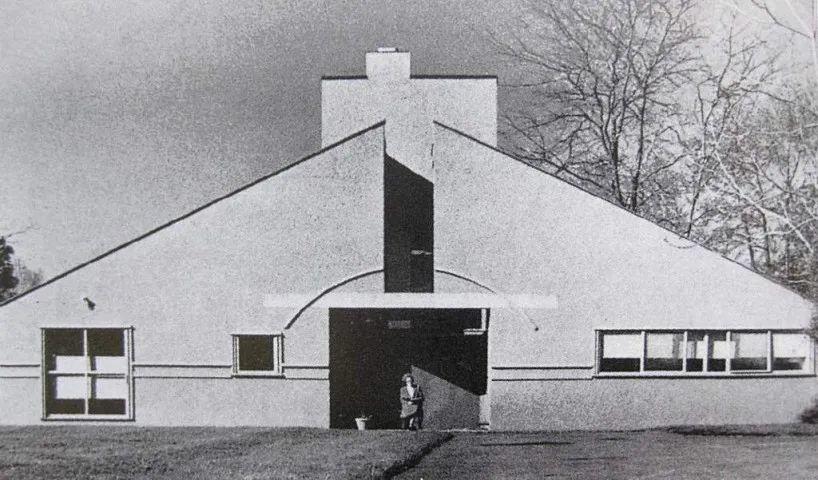

版权声明:本文由译者金秋野授权发布,文图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欢迎转发,禁止以有方编辑版本转载。若有涉及任何版权问题,请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快妥善处理。联系电话:0755-86148369;邮箱info@archiposition.com
投稿邮箱:media@archiposition.com
上一篇:伊东丰雄与竹中工务店合作方案:茨木市民中心地域改善项目
下一篇:李兴钢:圣徒的家园 | 北建大“二七论坛”第二期讲座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