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时间:2014年12月
李保峰,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他最近在为雅安地震灾区做幼儿园。他认为去工地是建筑设计不可分割的重要环节,设计对时间是无止尽的。彼得·卒姆托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建筑师,卒姆托设计的古罗马遗址博物馆也影响到了他自己设计的恐龙蛋遗址博物馆。他认为有些“绿色建筑”只关注“绿色”而忘了“建筑”,甚至“悄悄”制造问题,再“隆重”地予以解决。
有方:最近在做的项目是哪些?
李保峰:最近为雅安地震灾区做两个幼儿园。还有一个虽进展很慢、但与甲方沟通很好的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区区3700平方米,做了整整三年,设计及施工期间与甲方争吵不断,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有方:在拿到一个委托时,最先会做什么?
李保峰:通常会和我的研究生去现场,重点研究地形地貌及城市周边关系,分析任务书,挖掘可能的创新点。教师的眼界、经验加上学生因缺乏经验而不受约束的畅想,常常会导致独特的设计起点,可谓教学相长。


▲恐龙蛋遗址博物馆外景
有方:当项目进入施工阶段,会经常去现场吗?如去,通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李保峰:我认为去工地是建筑设计不可分割的重要环节。适应复杂地形的局部设计调整、对材料在真实环境中的选择判断、特殊做法的现场试验等,都需要去现场完成。我有过几次“关键时刻不在现场”导致的遗憾:有时是结构专业仅从结构角度作出的“正确”调整,影响了整体关系;有时是施工队为施工便利,改变了设计,监理公司却视而不见。所以,我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我认为关键的时候,常去现场。我的项目不多,每个项目去工地的次数恐怕都不下20次。
有方:最近在业务上最烦的事是什么?
李保峰:主要是时间与精力不够。发展中院系的行政管理耗掉太多时间,而设计对时间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尤其是扁平化小团队的带领者,个人投入的精力很大。我应该卸掉行政工作,专心做建筑师和教师。
有方:最近读的最有趣的一本书是什么?
李保峰:我上大学之前当过农民和工人,始终缺乏严谨的读书态度,欣赏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最近读了雷泽·梅本的《新兴建构图集》,该书虽名为图集,其实并不是工具性的, 相比 Kenneth Frampton 那本《建构文化研究》,它更针对数字化时代的新现象、新问题,读后引出许多超出建构问题的思考,更像一本关于数字时代设计方法论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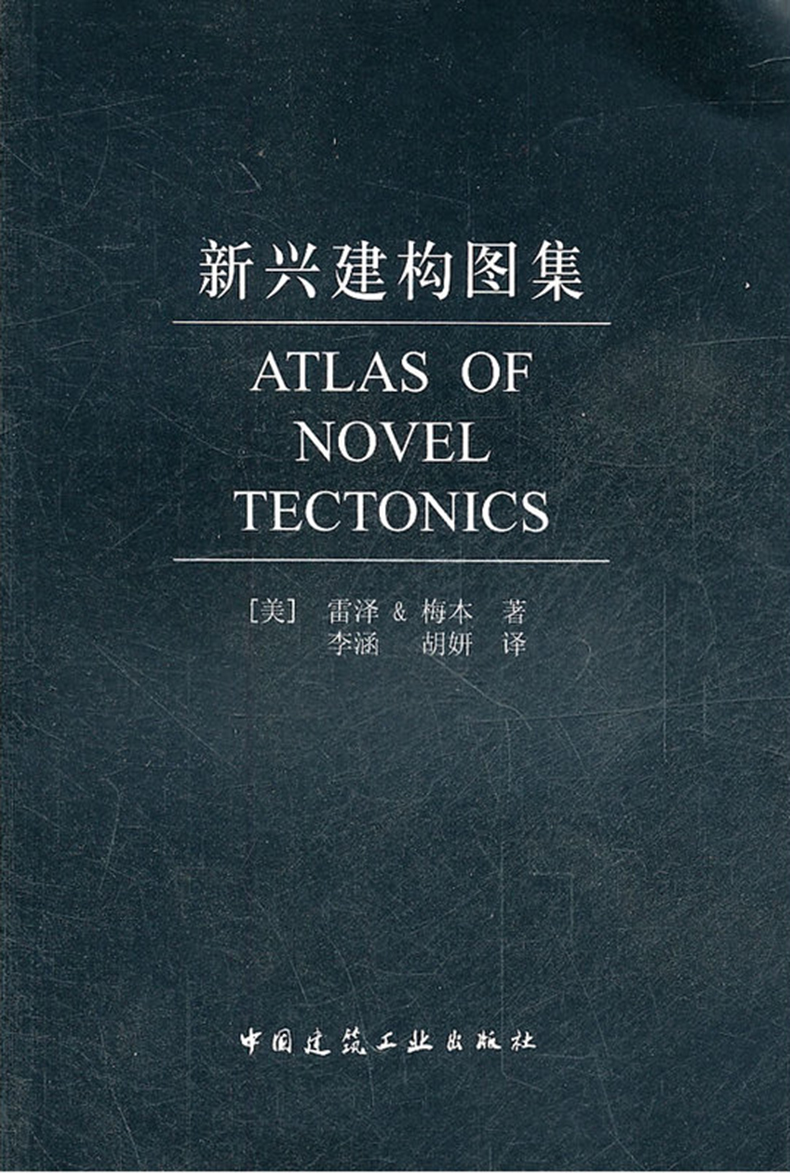
▲《新兴建构图集》封面
有方:最近一次旅行去了哪里?
李保峰:今年暑假去了挪威、芬兰、丹麦、瑞典和拉脱维亚,参观了一些大学,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获得许多新的城市及建筑体验。在建筑教育上也颇有启发,尤其是参观丹麦皇家艺术学院,那个早年培养出了老名星 Jo Utzon 和如今当红名星 Bjarke Ingles 的建筑学院,并没有因为出了几位大师就走向风靡夸张的名星风格,他们的教育仍然冷静地关注着建筑学和设计的基本问题。
有方:最近有没有新发现某位特别有启发的建筑师?
李保峰:华侨大学的尹培如,一个因地缘制约而难觅“高大上”甲方的年轻教师兼建筑师,其作品及文稿充满着真实和鲜活的思考。
有方:最喜欢的、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建筑师是谁?
李保峰:Peter Zumthor。我1988年流浪欧洲时参观过他设计的位于瑞士小城 Chur 的古罗马遗址博物馆:几个盖在古罗马墙基遗址上的简洁木盒子和一座插入其中的“桥”。我前年设计的恐龙蛋遗址博物馆,其概念便受到他的影响。我尤其欣赏他平和的心态,对场所及材料的巧妙挖掘,以及使用自然光的分寸。 还有一位德国老前辈,慕尼黑工大的Schröder教授,1988年夏天我请他给我开个书单,老先生给却我开了一个城市和建筑的列表,建议我不要闭门读书,而应亲身体验城市及建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参观了欧洲许多城市和建筑,那些课本中无尺度的照片、抽象的图纸和数字,与真实的感受逐渐建立了联系。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汉斯·夏隆的作品,那些貌似混乱的平面图、剖面图,却对应着精心推敲的、极其灵动的空间和秩序;那些平面上貌似随意的开窗和墙体,创造了动人的光影和对人之行为的引导。夏隆的作品使我意识到设计媒介之于真实设计的局限。旅行结束后,我明白了“行万里路”对于设计学习的重要性,此后便养成了旅行的习惯,终生获益。


▲恐龙蛋遗址博物馆细部
有方:最近中国建筑界哪种现象最让你反感?
李保峰:关注“绿色”而忘了“建筑”。 建筑学几千年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而非彻底自我否定的过程,建筑学中有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内核。绿色建筑本是对工业革命后过度消耗资源能源,及破坏环境的建筑设计方法的修正,但有些所谓的“绿色建筑”最终似乎要否定建筑学的本体及核心价值,评价建筑时动辄以“多少套先进技术”作为标准——采用技术越多,评价就越高;以至于足以用造价低廉的被动策略解决的问题,也使用复杂的成套技术,用高射炮打蚊子。有些“绿色建筑”则是先设计了不合理的玻璃盒子,然后再增加各种可调节外遮阳、双层腔、Low-E玻璃、地源热泵等昂贵的技术,以此显示建筑的“先进”和“绿色”。先“悄悄”地制造问题,再“隆重”地予以解决;这无异于先“偷偷”伤人,再“公开”救助,并宣称具有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怀。 按照仅仅关注绿色指标的原则,Louis Kahn 的建筑会因其体型系数过大而全部枪毙! 我的两位老师——Thomas Herzog 教授的“设计与技术整合”(而非堆砌)的设计方法,和清华秦佑国教授“要人文地学习建筑技术”的观点,在当下仍然具有启发性。
有方:上学时,哪门课让你最有兴趣,为什么?
李保峰:我1978年2月考上华南工学院时,中国刚改革开放,外语系教师几乎全是俄语背景,以至于第一学期竟开不出英语课,老师们第一学期自己“急用先学”,第二学期再对我们“立杆见影”。专业教师很认真,但经过10年浩劫,他们有明显的知识及眼界的局限性,有的老师还在使用诸如:“苏修的规范”之类的语言,设计课主要关注的是功能合理、方便建造及经济性,外建史课基本是照本宣科。至今还依稀记得看完那些模糊不清的黑白幻灯片之后的茫然。除了刘管平教授的设计课和陆元鼎教授的中建史以外,难有课程引起我们极大兴趣,倒是有些讲座很令人兴奋,如同济大学陈从周先生客串讲中国园林,美国德州大学 Burges 教授讲城市设计,听后方知,原来讲课也可以精彩。1982年之后学院逐渐引进了很多优秀老师,可惜我们已经毕业。
有方:最不愿打交道的甲方是什么样的?
李保峰:自己没想清楚却瞎指挥,其后又不断变换要求的甲方。 有时候换位思考,也理解甲方:作为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作为投资者面对效益的压力,他们不可能处处对建筑师言听计从,建筑师大可不必局限在自己的专业圈子里发牢骚。好在作为大学教师,我们可以有选择性地找投缘的甲方做设计。我去年完成的青龙山恐龙蛋遗址博物馆,业主是一难得的好甲方。这个项目仅以概念草图和工作模型便获得了理解,效果图是后来送规划局审批时才补充的。但这样的甲方可遇不可求。

▲恐龙蛋遗址博物馆室内
有方:最近哪件社会议题最让你关注?
李保峰:城市中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目前许多中国城市中的残疾人设施几乎仅是装饰,城市管理部门对改变残疾人设施状况的理由是方便管理——“管理方便”的权重竟高于使用者的需求;还有大量因开发而占据残疾人设施的现象,占据者振振有词,说经过政府批准,仅临时占用而已——资本竟然可以公然占据公共空间,践踏弱势群体。当下中国社会不乏高尚口号,却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
有方:最近除了设计外,花最多精力的活动是什么?
李保峰:学院管理、旅行和阅读。
有方:最近有没有对建筑设计感到困惑、厌倦,想过改行,改做哪一行?
李保峰:作为“双肩挑”的角色,教学及管理占用了大部分时间,我实际上没有太多时间做设计。好在个人没有太多对物质的渴望,在学校工作也无生产压力,所以我可以选择一些经济效益不高,但具有一定探索性的项目。这类项目往往周期长,需要更多的前期研究和后期现场服务。没有高强度设计的疲劳,也就没有困惑和厌倦。相反,我结合多年设计经验和教训,主讲的一门设计方法课,因不断得到当下设计问题的反馈而得以逐渐深化和充实,我反而乐此不疲。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学科,设计教学不能脱离当下中国的城市与建筑问题。
建筑师简介
李保峰
华南工学院学士,华中工学院硕士,清华大学博士;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新建筑》杂志社社长,《建筑师》杂志社编委,中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图片由建筑师提供。转载请通过邮件或电话与有方媒体中心取得授权。
上一篇:建筑师在做什么67 | 刘阳:主要卖艺,偶尔卖身
下一篇:尤恩·伍重的中国与未完成的悉尼歌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