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里我去了一些欧洲城市旅行,从冬天到春天,从对每个陌生地名的莫名紧张,到自由坦然地走在每一条行人语言各不相同的街道上。
那些精美华丽的教堂宫殿太多人歌颂了,它们是需要仰望敬畏的存在。
相比于复述宏伟,我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那些路上遇见的小房子。
它们杂乱平凡,但生动有趣,无比可爱。


意大利 曼托瓦
Piazza Arche

秋天的一个下午,朋友忙着做模型,我穿上大衣陪她的同学出门逛逛。
阳光毫不费力地穿过整个广场,刚收摊的集市还闷着人群温热的气息。
这个小镇的老建筑都是暖色的,墙面斑驳,像老人手掌一般,旧旧的温暖踏实。
小贩脸上带着红晕,和相熟的路人大声交谈。
穿着白色衬衣的金发女人踏着单车一晃而过,卡其色风衣被高高吹起,藤编车篮里放着一束花。
意大利 曼托瓦
Piazza Arche

很喜欢公爵宫旁边的一个小公园,树木高大坚实,远处低低的太阳为它们打下长长的阴影,投射在布满落叶的碎石地面上。
这里常常坐着一些老人,银白发梢在逆光里变成了金色,皱纹线条柔和,脚边趴着一只眯眼打盹的小狗。
偶尔也有眼神雀跃的青年,总是两个小脑袋凑在一起,没几句话就偷偷笑起来,然后更紧地拥过去,在额头落下一个吻。
从公爵宫绕出来,一眼看见了这个小房子。我跟身边的女生说,它们真好看,我要把它们画下来。她说,会画画真好。
她是一个学葡萄牙语的女生,几个月后我们在波尔图再次相遇,坐在超市吃面包夹烤鸡。
德国 法兰克福
Große Bockenheimer

德国的现代建筑给了我很多惊喜,高水平的工业呈现出一种关于精确的美感,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称得上艺术的品质。
那些反射着曼妙粉色,或是光洁如镜的玻璃嵌在一个个模数相同的方格里,映着周遭种种,像是把现代工业嵌入历史框架里的一段隐喻。
可惜圣诞节前夕的歌德大街十分清冷,大部分商铺没到中午就匆匆关门,我和Hanara只能在挂满节日装饰的大街上游走。
丢了手套又丢了帽子的我努力缩进外套里,只有橱窗里的食物看上去是温暖的。
意大利 威尼斯
Riva dei Sette Martiri

清晨我们咬着三明治走进满是游客的圣马可广场,一群海鸥突然俯冲进人群。一眨眼,地上只剩啄食残渣的鸽子和混战后纷飞的白色羽毛。朋友一脸错愕,手上空空如也。
后来我胆战心惊地攥着自己的那份,仿佛穿越围剿区,暴露在空地的我随时都会成为被袭击的对象。
在它们的示威下,没多久我就放弃了抵抗。找了个开阔地悄悄把食物放下,一路盘旋在头顶的大鸟们立刻飞扑而来。
想来这古老水城里的生物是从不怕人的,在威尼斯世代生存的骄傲足够让它们睥睨一切,尤其是我们这些闯入领地的聒噪外来者。
屋顶是它们的,塔尖是它们的,天空和海水都是它们的,我们手上的食物也是。
顺着水岸继续走,在去双年展的路上遇到一栋小房子,在游人如织的对岸兀自静立着,安宁得像一副油画,于此像海鸥飞鸣一样永恒。
德国 巴登
Seebach

驶出黑森林的时候我们丢失了导航信号,慌乱地开上了一条积满落叶的狭窄山路,直到被前方停着的车辆逼停,一个德国大叔扛着枪向我们走来。
几番交涉后才明白是我们误入了打猎的林区,好心的猎人掉头开路领我们出山,阳光在树林里忽明忽暗。
葡萄牙 里斯本
R.Cegos

从S.Jorge城堡下来的时候遇到街头艺人表演,在凸出的二楼小阳台上,手风琴伴着吉他欢快地摇头晃脑,他们用绳子吊了一只小桶下来装赏钱,整个转角都是快乐的。
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我想吃一个桃子。
走过长长的下坡路,这栋小房子的对面正好是一家杂货店。
买完桃子问摊主哪里可以洗水果呢?他说不用洗的,你看呀,然后顺手拿起一个,在袖子上蹭蹭就咬下去,满脸开心地看着我。
我捧着它上坡下坡,走了好远的路,时不时把它凑到鼻子前闻一闻 ,想起从前在大学专教,总喜欢在桌兜里藏几个桃子闻着来画图的日子。
后来在修道院前,同学们涌来向我道生日祝福,一个印度女生激动地问有没有party, 我咬着桃子囫囵着说:“没有啊。”
葡萄牙 波尔图
R.Escura

很多欧洲城市格局都相似,一条河流贯穿始终,老城被新城小心包裹着,而波尔图因为它的高低错落显得俏皮许多。
去主教堂的路上穿过了一条小巷,Escura在葡萄牙语里是幽暗的意思,可能指它狭窄无光也可能暗指危险。
但它是这样丰富有趣,每栋小屋或黄或蓝,贴着花花绿绿的瓷砖,鲜艳地挤在一起。狭窄的巷道仿佛开了窗就能伸手摘了对面阳台的花,头顶飘荡着晾晒的衣物和被单。
老人趴在小阳台上向下看,游人好奇地四处望,上坡下坡和出其不意的拐角里,所有的生活和路过都在这里重叠。
我走上主教堂一侧的石阶时,巷子口的店铺放起了歌,裹着围裙的女人、穿着运动服的青年,满头白发的老人纷纷伴着音乐跳起舞。
我站在高处看他们在小路上欢快地拉手转圈,抬眼看层层叠叠的小屋,被夕阳照亮的所有窗棂,橘红色的屋顶,偶尔惊起的飞鸟。
多好的城市。
捷克 布拉格
Golden Lane

布拉格城堡边有一条窄小的巷道叫做黄金巷,房屋低矮狭窄,这里从前是工匠仆人的居所,现在是一条纪念品贩卖街。
我知道卡夫卡曾在这里居住过,但一直走到尽头都没有发现哪一间挂着这样的标识。
于是回头数着门牌号又找了一遍,发现22号其实是刚刚走过的一间书店,他的小说集混在各种旅游图册里。
我在狭小的店铺里来回走,摸着桌上的书页,暗自思忖这里原有的布局,右边的空间只够嵌下一张单人床,桌子放在门口,门边最多挤下一个矮柜,再没有余地了。
好在有一扇小木窗,窗外紧挨着缓坡上的一片林子,树叶正衔着阳光摇晃。
这里更像是一个暗盒,故意压低了光线,框住一小块风景,望着那些流动的光线,身处的地方再昏暗好像都可以被原谅。
忽然有些理解他,“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意大利 维罗纳
Piazza Bra

从卡洛·斯卡帕改建的博物馆里向上走,站在狭窄的步道上可以看见像城堡一样的红砖老桥,有人在桥头拉着手风琴,鸽子从桥垛飞到屋顶上,对岸的城市像一座岛屿。
那天市中心的竞技场边在举行阅兵仪式之类的活动,满街都是身着正装的意大利军人,帽子边别着长长的羽毛。
乐团在市政厅前的宽大台阶上演奏着进行曲,广场上排满各个军种的装备展示,甚至还有为孩子们提供的各种体验游戏,装甲车边的士兵热情招呼着小朋友们来玩。
另一边的咖啡馆坐满了远远观看的人,有的士兵坐在台阶上吃冰淇淋,有的端着咖啡在队列里寒暄,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节日的笑意。
葡萄牙 塞辛布拉
Cape Espichel Lighthouse

我们坐了很久的车去看大西洋。
教授的本意是让我们去参观一座海角上的古老教堂,但我们一下车奔向了另一边的山野大海,这里是葡萄牙的最西端,也是欧洲大陆的尽头。
大西洋很平静,海面泛着细微的褶皱和银箔。近处海湾里的水面像一块祖母绿,被岸边白色沙石托起。
黄昏已至,裸露的岩石都被映成金色,草叶微微颤抖着。
我们站在山崖边,看薄薄的太阳一点点被吸入海面,最后一抹光芒消释后,海的尽头晕开一片温柔的粉蓝。
远处的灯塔微微亮着光,在玫瑰色暗沉的天空里,坚定而温暖。我们不知被什么感动,似乎只能用狂奔去抵消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
落在后面的我们一路欢叫奔跑着去赶车,穿过那座没来得及参观的教堂庭院,Yiwei跑在前面举着手机录像,镜头扫过我们因奔跑涨红的脸,挨个对着镜头挥手大声say hi。
那时我们胸腔里涌动着一种宏大的喜悦,因为不知如何表达,每个人都夸张地跑着笑着,想把二十多岁看过的这次日落咽进生命里。
怎样才算记得,怎样才能留住呢,那时总这样失落地想。
挪威
奥斯陆

坐到公交车终点站,再穿过一个小公园,草坡的尽头是属于挪威的夏日海洋。
沙滩上一家人聚在一块围毯边,三四岁的男孩穿着小短裤,举着水枪跑到浅海里准备和其他小朋友战斗,回头看见我,又害羞地别过脑袋。
我躺在沙滩上,拿帽子蒙住了脸,闭眼也是热烘烘的光线和海潮。
再睁眼的时候,一位身着连衣裙的老妇人拎着包走过,她在不远处停下,缓缓解开裙扣,里面竟是一件黑色的露背泳衣。她踩着温热的沙砾一步步走到海中,背影有些佝偻,白发颤动着,裸露的肌肤上是深深的皱纹,我被那样年迈的优雅迷住。
后来她坐回沙滩上,和我一样看向那些孩童,眼里沉着无边温和。
意大利
博洛尼亚

朋友从日本来意大利出差,抽空开车来看望我。
周六傍晚我们拐进博洛尼亚老城吃饭,这座以柱廊闻名的城市正值最热闹的时分。
我们费力地躲避着端着酒杯的优雅行人,让道于飞驰而过的单车少年,挤在狭窄的巷道里慌乱奔突。古老的沿街拱廊灯光昏黄,车窗外偶尔闪过身着长袍的酒吧青年。导航用日语播报着信息,让这个场景变得更加戏剧。
法国
巴黎

从卢浮宫出来已是眼花脚酸了,天气阴沉沉的,浮灰裹着冷风直扑到脸上。
拖着毫无兴致的步子向前走,忽然瞥见了左前方的埃菲尔铁塔。云层裂开些口子,阳光在铁塔后直射而出,塞纳河忽然有了光彩。
之后走的每一步,抬眼便能看见它。在餐馆小巷里,在林荫道上,它都会在某个拐弯后忽然出现在视野尽头,告诉你,也告诉每一个生活在此处的平凡的人,告诉那些天真或苍老的脸,你在巴黎。
登塔时天色将晚,几秒的黑暗后,蓝紫色的夜巴黎忽然跳出眼前,人群爆发出一阵惊呼。
铁塔是巴黎夜晚金色的脊椎,金水由此注入每一条城市的凹槽,滚烫地飞溅到周围的建筑上。我们还在上升,直到看见金色漫延到城市的尽头。
“如果你年轻时有幸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以后不管你去哪里,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我站在最高处的平台上微微颤抖。
丹麦
哥本哈根

路易斯安那博物馆离城区很远,下车还要走一段路,道路两旁排列着可爱的尖顶小房子,安静的庭院。
博物馆的门小小的,缀满了爬山虎。
中午听见有人在草坪上吹奏音乐,那人举着小号边走边吹,漫不经心地迈步,我和Clever跟上去。
穿过树林走到草坪开阔处,人群环出一个圈,几位音乐家站在当中,但他们演奏的不是任何耳熟的古典乐,而是自然宇宙的空灵回响。
水流和钟声合成电子音效,管乐间而吹出恢弘高昂的感叹,自由的,宏大的,我们仿佛突然掉落进宇宙的聚变中央。
人们端着午餐席地而坐,在阳光下安静聆听;草地上伫立着现代艺术装置,在风里轻轻摆动;背后就是大海,有船立着高高的桅杆缓慢航行,偶尔有快艇无声地划出一道白线;白色云朵低低的,一大团一大团地摞在海面上。
时间和空间在音乐里塌缩又膨胀,变得遥远。
瑞典
斯德哥尔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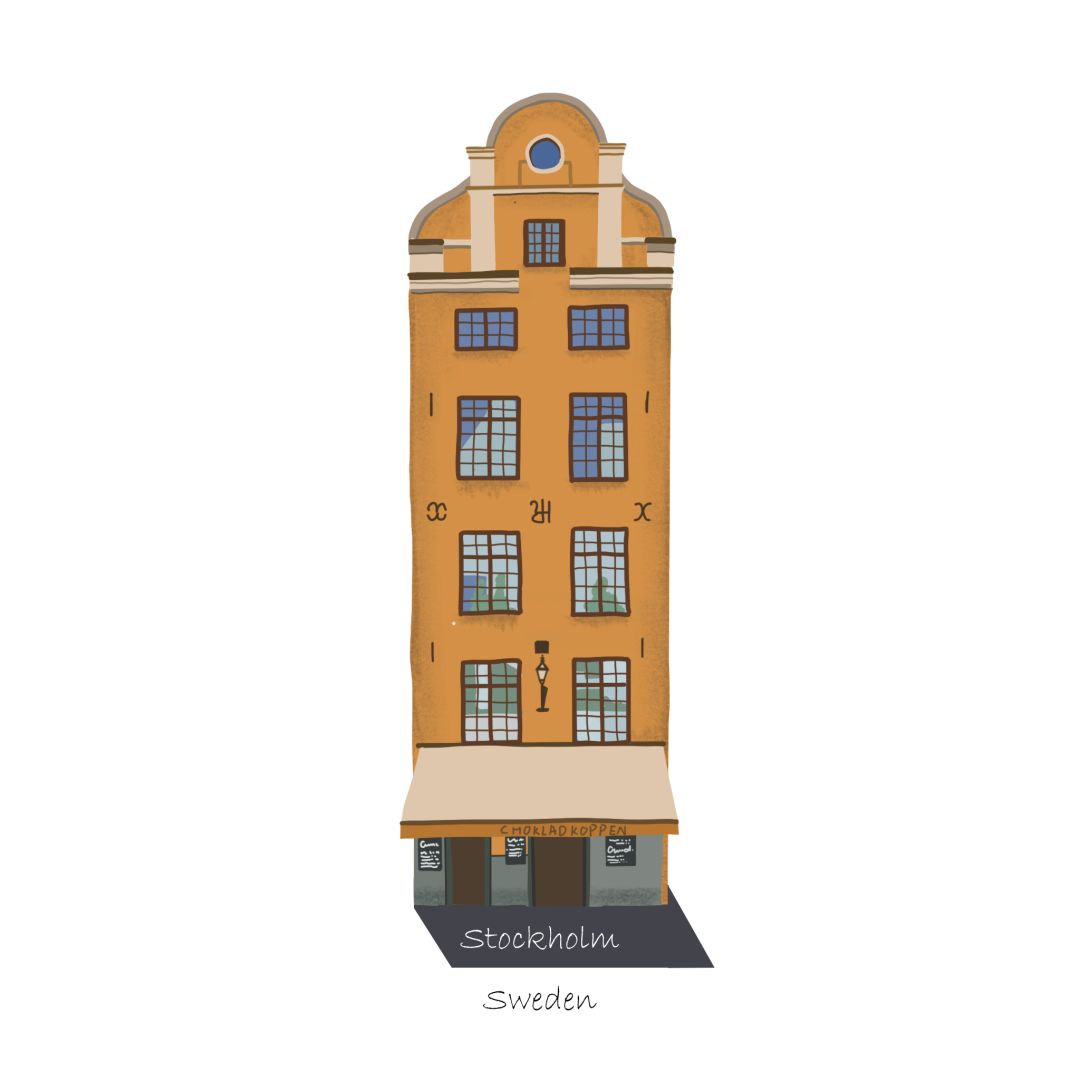
在瑞典见到了大学舍友。我们在老城里游荡,路过歌剧院,路过诺贝尔博物馆,路过宫殿,但一刻都没有停止交谈,任何风景都只能充当我们聊天的背景布,我们实在有太多话要讲。
去她住处的路上要穿过一大片齐腰深的荒野,小路上四下无人,我隐约觉得害怕。她却说习惯了北欧的无人静谧,就不会觉得寂静深处藏着什么。
傍晚拿着啤酒坐在海湾边的石头上,天空与水面是温柔的玫瑰色,一层层褪晕到岸边。
石头下的苇丛边有二十岁出头的女孩们在游泳,暗色里面目模糊,只能听见她们在高声笑闹,拍打着水花尖叫。
对岸灯火在森林里亮起。
意大利
博洛尼亚

很多人都知道“莫兰迪色系”,但不知道莫兰迪本人几乎终生都生活在博洛尼亚,画着他的瓶瓶罐罐,也画着他窗前的小路,几十年如一日。
他青年时也画过色彩艳丽的大幅风景,后来不知怎得,目光聚集到家中的几个瓶子器皿上,同样的构图同样的内容,总是时隔几年又再画一次。
我站在展厅仔细地看了那些笔触,边缘总是不肯定的,每一种灰色调都很复杂,那些颜色都是他细腻而温柔的注视。
我在一幅不出名的小画前驻足很久,画上是从他房间窗户看见的世界,说是风景有些夸张,因为那不过是几栋普通的褐黄色房屋,树木及道路,就像如今能在任何一个意大利的老房子窗口前看见的一样。
我笑着对朋友说,这不也是我家窗外吗。
可是他的目光比我深情得多。
那时我忽然明白,他画那些瓶瓶罐罐,其实也就画了万物。我没有去过他的故居,但我能看见他的画桌,和他看向窗外时沉静的眼睛。
奥地利
维也纳

维也纳的建筑很少用大面积彩色,大多是米白,立面总以砖砌线作精确分隔,专注于雕刻窗框和檐口,总有看不完的细节。
也许是因为复活节假期,整座城市除了游客聚集地之外鲜少行人,原本就干净的街道更是静谧,走在街上仿佛误入了电影置景。
偶尔出现在街角的集市小铺是为数不多的热闹,复活节彩蛋被盛在真的鸡蛋盒里,一层层摞起来供人挑选。从花纹到兔子,再到克里姆特的那幅《亲吻》(THE KISS),小小的蛋壳裹着这座内敛城市活泼的心。
挪威
奥斯陆

北欧的夏日凉爽,早晨骑车去看蒙克的画。
奥斯陆是山地地形,车子对我来说又大了一号,连续下坡里我紧绷着捏住车闸,几个拐弯下来胳膊酸痛。
穿过一片大草坡时我从车上跳下来,碾过地上的红色浆果,一路大喊大叫着努力控住方向,才不至于冲进湖里。
美术馆在一片绿地边,挪威政府和民众为这位国宝级画家费尽心思,经过几轮竞赛才定下了选址。馆里那副《呐喊》大概是怕被再偷一次,总有人眼神警惕地守着,连灯光都打得很暗。
只好去看其他展厅的大幅作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病中的孩子》,一瞬间被少女苍白脆弱的脸孔击碎。
我一直偏爱能够表达强烈情绪和氛围的画家,那些因为主观感情而扭曲的形体和绮丽色彩让我万分着迷。
总觉得面对画作那一刻的共情,胜过所有的精确。
意大利
佛罗伦萨

米开朗基罗广场所在的山坡并不陡峭,但爬上它还是得费些气力,每一步都坠着怕错过日落的急切心情。
登上平台时我才发现佛罗伦萨被山峦围绕,山上的小房子散落着,近处的河道向西延伸,直到融在夕阳的云雾里,每一座桥下都闪着光,模糊了一切坚硬。
城里朝西的墙面都像被刷上一层油,砖块都神采奕奕的。圣母百花大教堂被簇拥着,那座传奇的穹顶如今安静而温暖。
天色暗下去,台阶下有乐队在弹奏,大家坐在台阶上就着夜色欣赏,河岸边的一排房子都是金色的。
广场上有老人在拉小提琴,一对恋人腼腆地相拥着起舞,蹒跚学步的孩子被母亲拉着伴随音乐转圈。
翡冷翠古老而温柔的夜里,仿佛一切都值得被原谅。
意大利
米兰

常从米兰的机场往返,总会躺在朋友Hanara的床上短暂休息,睁眼时就会看见对街这栋房子。
每次看到它,意味着我即将前往另一个国家,或意味着我刚刚结束了一段疲惫旅程,对面阳台上的植物渐渐凋零又慢慢茂盛。
夏日的一个夜晚,我们从热那亚的海边回家,刚给从巴黎回来的Clever开了门,又有T带着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归来。而第二天一早,我们中有人就要去芬兰,有人要回美国,有人还在犹豫要不要回丹麦。
我们因为行程巧合而短暂相遇,站在过道里热络交谈,像回到从前的学校宿舍走廊,忘记了自己正身处异国,也忘记了几个小时后大家又要飞往不同的大陆。
凌晨三点,我在朋友房间赶稿,隔壁一间屋子睡觉,一间屋子聊天,剩下一间屋子的人坐在地板上围成一圈,用硬币占卜未来。
我写累了就走到他们身边,盘腿坐在地板上,在他们收拾到一半的行李旁,听人语气认真地问自己未来会定居何地。
大家紧盯着掌心的硬币落下,音响在中间跳跃着幽蓝的光,像是某种神秘仪式中围着的蓝色火把。
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被光照亮的侧脸,想到这个房间就是年轻与漂泊的核,忽然觉得宽慰。
这些都是从前的我,无法想象的生活吧。
图文版权©YENO野路
作者简介
孙小野
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历史及设计专业研究生,自由撰稿人
本文由作者授权有方发布,图文版权归作者所有,申请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
上一篇:经典再读43 | 罗比住宅:草原的线条
下一篇:夏洛特梅克伦堡图书馆新主馆:驶出“山脊线” / Snøhetta & Clark Nex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