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P,德国最大、最成功的合伙人制建筑事务所之一。这一成立于1933年的企业目前在全球设有12个办公室、逾6000个项目。自1997年起积极参与中国项目的国际竞赛,2006年起相继设立HPP上海、北京、深圳公司,设计项目包括上海浦东足球场、深圳北站汇德大厦、杭州阿里云谷办公园区、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心、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招商银行北京总部等。

9月20日,HPP总裁、高级合伙人约翰姆·福斯特(Joachim H. Faust),HPP高级合伙人维纳·苏柏(Werner Sübai),HPP合伙人库彦思(Jens Kump)造访有方并接受专访。从这一已有86年历史的德国老牌建筑事务所的制度背景、设计坚持,到其在中国的设计策略及对市场的理解,下文及视频将由三位高层分别展开。



有方 自1933年于德国成立至今,HPP已有86年历史。对于建筑事务所而言,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于这一持久性,您认为有哪些支持因素?
约翰姆·福斯特 1933年,33岁的Helmut Hentrich建立了个人事务所,但很快意识到与人合作比单打独斗更能让公司有好的发展。于是在1935年,一个新合伙人加入,自此HPP开始以合伙人制公司发展起来。在过去的86年里,HPP的发展与合伙人制度的成熟紧密相关。这一机制带来了很多方面的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多元思考方式的引入。
直至今日,HPP内部仍会对每个项目进行充分讨论,我们不是只有一种建筑表达,而是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其中的一个准线是,HPP一贯坚持完成高质量的建筑。“高质量”体现在建筑的个性、高辨识度层面,以及对细节和建造质量的要求。这些特质让HPP成为一家在全球范围内能为业主所信赖的事务所,对质量的重视,是HPP领导人如父亲般自创立之初的告诫,我想这种特质也会传递给企业的下一代,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四代。



有方 回顾这86年历史,您认为建筑设计公司应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
约翰姆·福斯特 保持年轻。
我们一直希望有更多年轻设计师的加入,询问并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时候作为设计领导,我们常反思自己是否仍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为年轻人的成长速度非常快并且在不断地打破传统观念,我们也需要据此调整自己的认知。
而在另一方面,遗产与传统也是建筑学的重要因素,每个城市的居民都希望保留其生活空间的记忆与辨识度,如果非常激进地将所有传统的事物和地标都清除了,那么城市的个性也会消失。所以年轻激进的想法与古老传统之间的交流,就非常重要——它是能帮助找到好的设计方案的奇妙因素,一方面满足历史与“身份”的见证,同时为未来找到出路。
有方 您是HPP的第4代领导者,而HPP的每一届领导班子之间,是如何选择、传承?
约翰姆·福斯特 我们的每一任总裁都有一个共同点:在HPP企业内部成长起来。我们很少选择成长于团队外的设计师担任决策者,尽管他们可能是被HPP文化吸引的优秀人才,但我们的领导者身上必须带有HPP自己的基因。
这种“基因”就是我前面解释过的,合伙人制要求的多样性——在综合多种意见后做出最佳决策,同时不能失去带来创新和自由思想的冒险精神。自由思想一直是我们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尽管我们内部需要达成共识,但仍不断会反问自身,这是最合适的方案了吗?是否需要从更开放的角度重新思考?对HPP而言,这种关于设计的讨论极为重要。

有方 对HPP合伙人制度的优势我们已有了解,那么在您总领团队的22年中,是否曾体会到这一制度的局限?
约翰姆·福斯特 当然。合伙人制的一个问题在于,它要求决策者不断与拍档协商设计方案,对一致的追求中有时就难免妥协。而如果是明星建筑师独立决策的机制,决策者可以实现更激进的想法,最终结果会与个人意愿更加吻合。合伙人制度要求避免个人主义,参与者需要从集体角度思考;由此带来的一个风险是,我们可能会失去更为激进的想法和立场。
除此以外,我认为HPP依然能够快速决策、达成一致、和而不同。比如我和苏柏(我们的下届总裁)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总体来说,我认为合伙人制度的要求不是一种缺点。
有方 作为德国重要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领导者,您认为“德国建筑”的特质为何?HPP希望传递的又是什么?
约翰姆·福斯特 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德国工作,有大量的标准规范需要遵守,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过多了。标准的数量不断在增长,而我们一直希望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以更简洁的程序与系统来取代当下已成为建筑师负担的标准体系。
比如说,如果你需要在德国提交一个普通建筑的设计申请,你得考虑到的就包括LEED银级认证的要求。这是德国建筑业的现实情况,方方面面都有着规范的限制。这也是德国建造成本非常高的一个原因,标准被提升到了让人怀疑是否必要的程度。
我们有关于能耗的标准,针对隔音的标准,比如不应让酒店住客听到隔壁房间的关门声,而如果我住进美国哪怕较新的酒店,我或许都能听到隔壁住客去盥洗室的声响(笑)。这一套复杂的标准体系,是德国建筑环境与全世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的地方。
相较于开创新的建筑发展道路,在德国做设计时,我们更常思考的是如何应对规范标准与建造成本。这就像边踩着刹车边开车,受到着很大限制。我总是希望德国建筑师可以突破这个困局,有更多的自由,但这就是目前德国建造和组织的方式。

有方 在中国做设计时会更自由吗?
约翰姆·福斯特 好像是的(笑)。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重心更多是在方案前期及初步设计阶段,对施工图以及实际建设的涉及较少。但我们非常希望能更多地参与到施工阶段,因为这样更能确保最终成果与方案的一致,而不是在建造中丢失细节。
有方 HPP目前在全球共有12个办公室,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沟通。那么在你的观察中,近年国际建筑学领域有哪些好的变化?又是否有需要警惕的趋势?
约翰姆·福斯特 我想从需要警惕之处谈起。我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建筑设计愈发相似,不管你是在美国、德国、中国、法国或其他地方,建筑设计都面临着日渐趋同的危险——在建筑表达层面,目前很难看到积极的趋势,在各国多是同一种语言的复制品。
一个我很认同的“反例”是中国建筑师王澍利用拆迁回收材料设计建造的宁波博物馆,他使用了与本地建筑的材料、特质、表达有关的设计语言。这种“在地化”实践在德国某些地方也依然存在:德国有不同的州,南北差异虽然正在缩小,但仍较明显,不同城市仍有一些特定的常见材料。比如基尔(Kiel)或吕贝克(Lubeck)多用砖材,而今日的法兰克福则主要是国际式的高层建筑,当地的原始建筑已近消失。我认为这种“在地化”是今日建筑师在不同国家、地区工作时需要重视的。
好的方面在于,全球建筑的整体水准在平稳提高,这体现在质量、可持续性、结构安全、逃生通道要求等方面。现在,如果我们在中国建一座体育馆,其建造标准和在米兰、德国或其他许多地方是一样的,人们因此可以相信自己能够安全地使用现代建筑。
有方 造成这种高度重复的原因是什么?
约翰姆·福斯特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家都太想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了。当许多建筑公司都在为国际知名度而努力之时,作品的认可和识别度往往依赖于建成的高层塔楼等人们已熟悉的建筑类型,重复性也由此而来。这也是王澍的建筑让我十分惊喜的原因,因为他的设计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样的设计需要得到媒体和建筑界更多的关注,因为对建筑业来说,对“难以复制的表达形式”的寻找,有很高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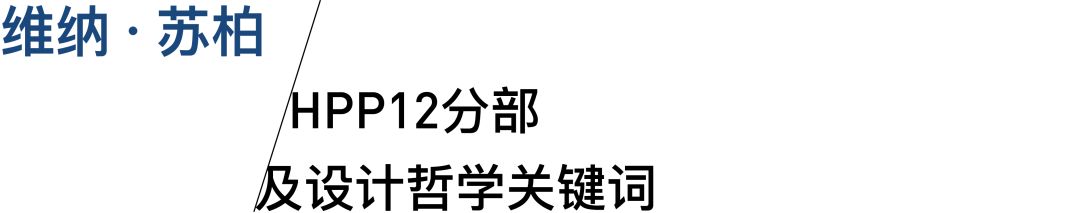
有方 那么您呢,苏柏先生?在您的观察中,近年国际建筑学的发展有哪些好的变化,又是否有需要警惕的趋势?
维纳·苏柏 我的看法跟福斯特有些不同,我认为目前的国际建筑实践有很积极的一点,即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建筑师确实可以互相学习,而且我们可以作为个体,独立地进行体验。的确,不同地区之间的学习也带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重复性;但正因为当前的开放,我们得以在德国之外的地域设计建筑,并在不同实践中建立关联,将“德国设计”带到其他国家,同时向其他国家学习并把经验带回德国。这一更为丰富的实践体验,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设计水平。
需要警惕之处则在于趋同性,但我相信我们可尽力避免。从全球范围看,人们不断向城市涌入,城市化进程迅猛,这意味着在文化层面我们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也有着类似的问题和需求。
总体来说,对于全球化开始后至今的局面,我仍持较积极的看法。我们的环境和体验都更为丰富,而问题在于,如果不加以重视,我们会失去原始的、本土的方法与传统。这可能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关注全球化需求的同时,理解每个具体地域的在地性。

有方 那么当来到中国,HPP会否针对中国项目改变设计策略?
维纳·苏柏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彦思随后也应该给出他的答案。我们负责HPP在中国的建筑实践,已经二十年了。前十年,我们主要在德国对中国项目进行操作和指导,不管是设计层面还是内容层面。而后在2006年,我们于上海建立了HPP中国公司,此后HPP在中国的项目更像是“中国制造”而非空降自德国,而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办公室,也可以从中国得到许多教益。
我认为这中间的区别,或者说正确结论,并非“HPP在中国的设计方法与在欧洲的不同”。更有趣且重要的一点在于,作为一个跨国设计公司,我们在不同地区的实践共同支持着HPP整体的进步。各地最终的项目成果体现着设计对具体任务要求的回应,HPP中国的项目经验,也深刻影响了我们在其他国度的作品。

有方 提到这个,我一直很感兴趣的一点是,HPP如何选择分部的地点?在德国你们成立了8个办公室,而在国际上,你们尚未选择欧美,却来到了土耳其和中国。
维纳·苏柏 (看向福斯特)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吧?我想说,我们很快会有新动作了,虽然目前还处在保密阶段(笑)。
约翰姆·福斯特 其实合适的机遇是我们设立分部的最主要原因,比如在伊斯坦布尔和上海、北京、深圳,分部的成立往往是遇见好项目及人选的机缘巧合,而非长期谋划的结果。
我们在俄罗斯有项目,也常常考虑是否该在那里设立分部,但俄罗斯的市场运作模式让我们有些犹豫。尽管如此,我们仍在努力抓住俄国的机会。我觉得地点不是问题,如果能遇到古巴的项目,那我们就去古巴,还可以抽些好雪茄(笑)。

有方 当HPP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着规模各异的诸多项目,你们是否有一以贯之的设计风格?
维纳·苏柏 HPP选择的是以人为中心、对环境友好的设计手法。我们最关注的是建筑与公众的相关程度,而不是外形和单纯的“设计问题”。对我们来说,建筑外形的雕塑感及其与其他楼房的区别度,是次要的考虑。
有方 您曾说“遗产”与“创新”是读解HPP设计哲学的关键词,具体如何理解?
维纳·苏柏 我们可以历史建筑为例,这类建筑可以再分为两部分,一种是纯纪念用途的场所,另一种则与公众有更紧密的关联。纪念类历史建筑一般与文化、宗教、传统有关,它们经历了漫长时光的洗礼,其外观和功能都因象征着权力、宗教等力量而得以保留,但如今只具备纪念性。第二种历史建筑是功能已改变的那类,但恰恰因为这种转变,建筑仍然保有动态的活力,与公众保持着联系。它们的幸存不仅是因为具有纪念性,更因为其仍可使用。
一个历史建筑与创新用途结合的好例子是我们的杜塞尔多夫城市音乐厅项目,它曾是一个天文台,用于天文观测及研究,后来在“二战”中被毁坏。我们的想法是将其改造为音乐厅,经过精心的再设计和空间规划,这个前天文台被创造性地改造为一个新景点,同时满足了文化用途和公共需要。


另一个稍偏商业的例子是位于杜塞尔多夫的“三片楼”(蒂森总部大楼)。它最初是一座为蒂森公司设计的单一功能地标建筑,曾作为这个著名跨国钢铁公司的总部大楼,是德国战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在2010年蒂森总部搬离后,我们对其进行了改造:翻新后的平面布局及外观都被完全改变,每层可分割成2个以上的出租单元,可供不同公司租赁使用。这再次体现了建筑灵活性的优势以及活力——建筑可以同时是在城市中指引方向的地标,又是在用途上与时俱进的场所。


约翰姆·福斯特 苏柏提到的杜塞尔多夫音乐厅是体现HPP历史建筑改造思路的好例子。它曾是个古老的天文台,而更新的剧院室内设计将天文台引人遐想的气质保留了下来,内部就像是只有微弱星光点缀的深蓝色天空,身处其中仿似看着真正的星星,天文台的魔力依然存留。

有方 HPP对于BIM有很好的应用,也与UNStuido等事务所在多个项目中通过BIM进行合作,您目前如何理解这一技术?
维纳·苏柏BIM是一种方法,它与最初的设计规划及建造无关。这就是我认为在谈论BIM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对BIM的使用只代表着我们的设计方法从非数位(analog)向数字化转变,就像从手绘图纸到电脑绘制的转向。BIM和3D技术改变了建筑师的工作方式,首先这体现在3D建模对绘制平面图的替代——对今日的建筑师而言,后者可能不再是最重要的工作。

而在工作流程层面,BIM的使用改变了原有的流程顺序,信息建模重组了整个设计过程。例如,对细节的思考和精确设计被提前到了设计的早期阶段,即使还没到考虑施工的环节,细节也需要被准确地表达,否则无法为后续阶段建立模型。BIM带来了一种新的设计方法,它需要遵守许多规训,然而这样的工作流程有时与创造力是相悖的。
我认为在目前阶段,建筑师对BIM的应用还停留在建造出项目的1:1虚拟模型——它可以非常精确,然而我们如果没能在深化阶段充分利用好这一模型,那么对BIM的使用将只是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当业界能充分地理解BIM并在实践中发挥出其优势,它将带来巨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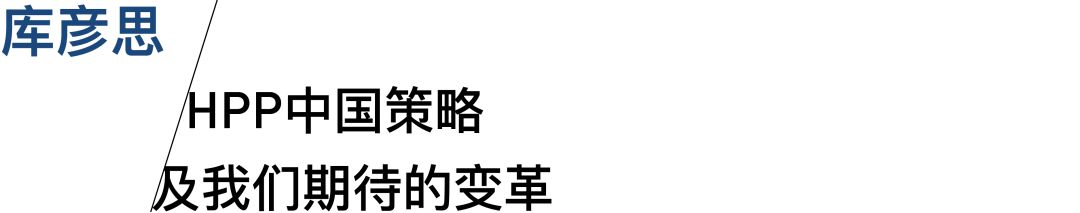
有方 HPP第一个中国办公室的成立,是出于何种契机?创始阶段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库彦思 HPP对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早在我加入公司之前就已存在了。我还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就读到了HPP一位股东发布在德国杂志上的关于1998年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国际竞赛的文章,提到HPP当时非常努力地参与了(笑),但最后也只是成为进入第二轮设计的国际事务所之一。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中国建筑市场非常好奇。在2002至2004年期间,HPP开始在中国市场斩获成果,我也开始对接中国项目。2006年,我们赢得了两个机会,一个是德国汉高在中国的亚太总部项目( The Asia-Pacific Headquarter of Henkel),另一个是上海世博村国际竞赛中的胜利。由此我们决定于沪设立第一个中国分公司,HPP上海。
起初最大的困难在于,HPP在德国是一家知名企业,也有客户的信任优势。然而当来到中国这个全新而庞大的市场,这一优势近乎消失,我们需要从原点开始一步步赢得名誉并切实建造出项目,而这需要时间。起初的五年非常艰难,因为我们没有项目建成,只能展示虚拟方案;HPP强调的是质量,却没有可证实品质的落成建筑,无法在中国境内证明实力。现在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与客户的沟通也更轻松,因为我们在中国也有了诸多类型的项目建成。




有方 自您2006年来到上海、建立HPP中国公司以来,在与一个新的中国客户初次沟通时,您通常会如何介绍HPP?如何呈现这个国际事务所的特点?
库彦思我认为HPP的特点在于,设计方法非常注重建筑的耐久性及长生命周期,我们对于“什么是建筑的寿命与质量”有深刻理解。但是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需要同样在意建筑耐久性的甲方,所以通常如果甲方对这方面有了解或者需求,就会与我们联系。
此外,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的建筑环境下,设计过程更加灵活且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客户对于速度也有更高的要求。所以HPP组建了自己的中国办公室,团队中有核心的德国建筑师,而与中国客户的日常联络对接则由中国办公室直接负责。这一团队结构与工作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并能避免时差及交流中的误解。

有方 为何决定于9月成立在中国的第三个办公室,HPP深圳?
库彦思 就像之前提及的,拥有了互相信任的客户并希望与之更紧密地合作,是我们成立HPP上海的原因。而现在我们有一批关系紧密的客户在深圳,这也是我们建立深圳分部的初衷,是对市场的直接回应。
另一个原因是对于深圳的好奇,我们相信能在这座城市学到很多。即使在全球范围内,深圳都是一个独特而近乎传奇的现代都市,这里有着极为蓬勃的建筑实践,会启发更积极而具批判性的建筑思考,让我们重新审视如何建造、如何回答有关空间和建筑的问题。来自全世界的建筑师可以于此互相学习——在建造的同时向市场学习,对HPP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约翰姆·福斯特 对于这一决定我想稍作补充。HPP在德国有8个分部,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么小的德国成立8个团队呢?因为我们需要和客户、当地政府及市场都保持最紧密的联系,这样才有可能发现更多潜在的机会。在德国这样一个较小的国家中,先深刻理解一个市场、再进入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德国的每一个分部中,都有非常熟悉当地方言和环境的员工。
而当来到中国,HPP或多或少依然是一个“异乡的外来者”,是一家德国企业。我们可能与中国本土的设计团队一样,有深入了解这个市场及其期望的可能,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数年的时间与更多的努力。

有方 与客户的紧密沟通是HPP一直强调的,那么在您的观察中,中国业主对于建筑的要求,在近年可有变化?
库彦思 中国业主的需求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仍然希望得到惊喜,一天中能有两次惊喜就更好(笑)。而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十余年间,中国业主团队的专业度有着非常明显的提高。决策者和此前一样,对全球市场有全面的认识;而目前更有帮助的是,业主的管理层和直接对接人员,也都十分了解国际水准的质量,具备非常高的专业性。由此我们可以在不同层面上,都展开同步的对话。
约翰姆·福斯特 而就像习主席此前的表述,“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质量比数量重要”“应更注重建筑的功能性”等等,我认为HPP的设计理念与这些原则是相符的。HPP不是“杂志封面建筑师”,相较于炫丽夸张的外观,我们更认同谦逊适度的手法。

有方 对于方才苏柏留给您的问题,“HPP在中国进行实践时,会调整设计策略吗?”,您怎么看?
库彦思 我们需要做出一定调整,因为与中国客户的关系和交流方式会有些不同。在德国,甲方通常非常专业,在项目开始之前便会自行调查并研究建筑条例,对如何实现项目成果有所了解。所以在德国的设计,更像是与客户一起回应建筑业严格的规则,再使最后的成果成为艺术。
而在中国,这个过程会更灵活,许多甲方希望建筑师能够提供灵感,在设计的过程中进行决定。这样的方式要求坦率的沟通、相互理解和大量的交流。所以总的来说,在中德之间,建筑师与客户的关系及各自的角色,都有很大差异。
有方 在带领中国项目的过程中,如何保证设计的完成度和最终质量?
库彦思 这是个有些难回答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需要有正确的客户找到我们,因为当时我们作为小型的外国建筑事务所,很难签下有权控制最终建成质量的合同。我很希望这个现状能够改变,希望中国的合同法允许我们也介入并承担起质量控制的责任。目前,我们需要和客户团队合作,从而保证我们的方案能够被完整执行;否则,就算我们是老虎,也没有能去撕咬的牙齿。
HPP中国起初只有5个人,而现在已经有105位员工了。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进入另一个阶段,更完整地将我们在德国的实践方式运用于中国,提供与德国项目一样的严谨工作、同样质量的方案和控制力。但这也需要合同制度的变革。
有方 在HPP擅长的办公建筑、体育建筑、改造及文化建筑中,可否各推荐一个您个人最喜欢的?
库彦思 我最喜欢的办公项目,可能是HPP上海办公室(笑),因为它完整记述了我们的成长故事,非常有活力。而在我们为客户设计的项目中,我很喜欢的是上海地产中企·华润未来世纪大厦。我们都知道,浦东有太多300、600米的高层建筑,而一座50米高的建筑要如何与这些塔楼竞争?我想我们最后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该项目也很好地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在办公室就能很好地欣赏到黄浦江的景色。


在体育建筑中,我最喜欢上海浦东足球场。这个建筑有很友好的近人尺度,同时能满足人们日常使用的多种需要。

文化类建筑的推荐是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在未来两年内,它将逐渐成型。这是教育建筑的一种新类型,将公共空间的品质与“学习超市”一般的多元场地结合在一起。


之于改造类项目,我很喜欢的是我们2018年年末完成的上海滨江道办公楼,是对黄浦江畔一个仓库的更新。历史建筑的结构元素和特质被很好地保留,最终转变为氛围良好的现代办公空间。HPP负责了这个项目的整体建筑及室内设计,当室内部分也属于我们的设计范围,我们就能对合同框架本身无法保证的最终建成质量有更好的掌握,对与建成品质相关的决定,有更大的影响力。



出品 | 赵磊
采访及撰文 | 原源
视频制作 | 郭嘉
摄影 | 胡康榆
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
欢迎转发,转载请联系有方新媒体中心。
上一篇:大空和大地保育园:城市与公园之间的“家” / 木下昌大建筑师事务所
下一篇:有方 x 一言一吾 | 阿尔瓦罗·西扎:我的建筑中没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