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9日,在小雪后的苏州拙政园园林书房,借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童寯撰写,童寯之孙、同济大学教授童明翻译的新版《东南园墅》书籍发表,引出茶桌上一场关于园林与建筑的讨论。到场的学者、建筑师足有三十余人,作为主持的童明感叹:上一次建筑师齐聚讨论园林已经是11年前的事情,此次在拙政园再续讨论,尤显珍贵。
童寯,建筑学家、建筑师、建筑教育家,与吕彦直、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我国近代造园理论研究的开拓者,著有《江南园林志》《造园史纲》等经典作品。《东南园墅》是其晚年于病榻上用英文书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意在向西方介绍江南园林之美,是其近半个世纪研究的结晶。

讨论伊始,童明先谈了一段往事,他表示这可能是童寯第一次受到园林给予的触动,从而促使了后面研究的启动。那是1932年,童寯与陈植陪同在纽约工作时的老板伊莱·康游览苏州园林,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天。惊讶于一位西方绅士站在完全陌生的中国园林里,却深受感动,呈现出如此亢奋的状态,以那次触动作为契机,童寯开始了对园林漫长的研究。

相比完成于1937年的《江南园林志》,《东南园墅》直至童寯去世前才完成,初次出版是在1997年。童明表示《东南园墅》的准备时间可能更长,开始得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早——在1936年的《天下》月刊杂志上,童寯发表过一篇介绍江浙地区园林的英文介绍。这篇论文开篇很大一部分,就是后来《东南园墅》书里的核心内容。
童寯作为一个建筑师,面对一个相对陌生,有一点久远距离,但同时又植根于自己内心深处的兴趣,其对园林的研究不完全体现为历史性的梳理或者是考古性的挖掘,而是以建筑师的视角来关心如何营造园林。这就构成《东南园墅》的独特之处——它不仅是关于东南地区园林的历史性梳理,同样也是一本关于设计的理论性著作。



最后谈到童寯为《东南园墅》起的英文标题Glimpses of Gardens in Eastern China中“Glimpse”一词,童明表示,这“一瞥”,似乎正是观看园林的最佳方式。它好像描述了一个奇妙的场景:一群外国人透过门洞一瞥,看见江南的园林,带着惊奇与赞叹。
作为新版《东南园墅》的两位序作者,王澍与董豫赣在现场起头,各位学者、建筑师陆续分享了童寯的园林研究给他们自身带去的巨大影响,以及作为建筑师,为何今天我们需要讨论园林的话题。

“童明让我给新书写个序,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大概是1997年的时候,我开始对中国园林产生兴趣。之前的《童寯文选》只是一个出发点,直到《东南园墅》,我前后共读了6遍,读完才真正有了觉醒的感觉。大家都在谈园林,但此谈(童寯谈)和彼谈(别人谈)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杨廷宝主要做设计,关于园林没有留下太多研究;梁思成研究历史,基本不做设计;又做设计又搞研究的就只有童寯,而且童寯的设计还做得特别好。
园林是高手做出来的东西,它一定是要再碰到高手的时候才看得明白。否则光研究了一堆知识,都不能让园林再次焕发生命。但是童先生就有这个能力,他是非常好的建筑师,有非常好的眼光,以做设计的体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比如,“情趣在此之重要,远胜技巧与方法”,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基本变成了建筑理论的基点。我当时写《造园记》的时候把情趣拿出来谈,所有发生的事情就被点燃了。又比如,“中国园林中,建筑如此赏心悦目,鲜活成趣,令人轻松愉悦,即便无有花卉数目,依然成为园林”,这句话把现代建筑和园林之间的界限打破,后来我在做现代建筑的时候就敢做,直接和园林对话。”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我想造园。我读童寯的书,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中国园林的分类。他认为没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宗教园林、北方园林、南方园林、所有的园林都是一样的制式,这就避开了与造园无关的设计的分类,而直接切入造园制式的方法讨论,它才能指导设计。
这让我想起写日本建筑史的关野贞或者是太田博太郎等人,他们认为平安时代后日本建筑的主体已经从宗教建筑转移到了居住建筑,这样的讲法,与西方现代建筑从宗教建筑到居住建筑的语境相吻合,并预留了日本现代建筑设计的接口,而非纯粹的史学分类工作,它让筱原一男宣称‘住宅是艺术’的样式研究有着明确的史学支撑。
日本的建筑史有着建筑师设计的现代视角,而我们的园林史大都还在按所有权来分类,从中几乎无法判断园林的价值,也就难以对造园一事有实际帮助。
不管是《江南园林志》还是《东南园墅》,既有建筑史的分量,但又能对造园设计有所启迪,这才是它们最重要的价值。”

“童寯是优秀的建筑师也是优秀的史学家,开拓、引领、贯通、慎独。
开拓,因为童寯是现当代里用世界眼光来研究中国园林的第一人:从宾大回来,和美国建筑师跑了一趟,想到了很多问题,不仅限于历史层面的考究,还把中国园林纳入现代建筑层面上来思考。
引领,后人做的研究都是在童寯的引领之下才展开的,包括陈从周等人。童寯在前面做的工作特别重要。
贯通,童寯的贯通能力确实是我们都做不到的。世界史的眼光,贯通中西,需要科普的时候就讲科普,需要深入探讨的时候就深入探讨,随时切换。
慎独,童寯是非常严谨的研究学者。不像今天的我们,稍微做出了一点成果就开始大肆宣传,甚至还有成果未出就开始各处宣讲的。童寯不一样,他做研究做完了也不说,从来都是踏实低调。童寯可以仰望但不能学习,学不到。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不去学习了,我们还得慢慢学,慢慢改。”

“看童先生的书,最受启发的,一是他思维的切换,经常把古代的事物和现代的现象、中国的与国外的历史进行切换,十分自如;二是童先生不像一般人做园林研究做着做着就掉进去了,甚至变成自娱自乐,而他总能够站在外围看待园林,好像有另一双眼睛,非常冷峻,评论园林也非常到位。”

“童寯先生的园林研究,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态度,既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十分珍惜,又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状态中,这点非常重要。他对各种文化中的园林,对画,对看或者是观,都有同情之理解,加上他对设计的深入理解,所以能做出通透的研究。
在我所阅读过的童先生的书里,包括他薄薄的《造园史纲》,深深觉得,惜墨如金是一个多么好的学术品格和习惯。面对园林完全可以有大段的感慨,但这往往会导致不确切,而童先生总是能用非常少的语言,把思绪、情趣、眼前的事物贯通在一起。他的文字跟他所描述的事物,好像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可以说,我心中的中国园林,有的是自己看到的,有的来自书籍,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来自童先生运用特别的语言和图所描述的园林。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我影响很大,我愿意继续在这个道路上学习,也愿意尽可能地传达给我的学生们。”

“前几年我在研究留园近现代变迁情况的时候,对照童先生的《江南园林志》来看,发现几处有趣的细节:在还读我书处有一个比较小的立交,上了一个坡,不知不觉到了二楼。看童先生的图画了一个剖断线的符号,虽然是步测手绘,但非常精确。直接看图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对着老照片反推的时候才发现。但是在精确观察的前提下再来看《东南园墅》,我们却没有看到童先生因为对细节的熟悉而在讨论非常技术的问题,反而是回到一个非常放松的思考状态。这让我想起在英国的时候,经常看到18世纪英国贵族们(例如Sir William Temple和Joseph Addison)讨论园林的文体,状态介于散文与杂文之间。这些文章不怎么关注具体的园林细节,而试图在概述的层面指向更大的深度。正因为不是具体的,是宽泛的,反而似乎能够看到一种思考的痕迹,书写本身成为一种思考。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书,大部分都呈现结果,童先生的书能让人看到思考的痕迹。
另一方面,我觉得童先生不是一个研究者,也不是一个理论家,非常像是一个超越了具体知识的人文主义者。在我看来,《东南园墅》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思考的轨迹。这可能恰是最有意义的地方:不再讨论“苏州园林”或是“中国园林”,他讨论的是人跟园之间的关系,超越了文化的差异,正因为如此,被讨论的对象才变成了世界性的东西。真正世界性的思考不一定非要基于抵抗、差异、比较。当你超越之后抵达一个自由的状态,反而帮你获得真正的认识。这点跟前面我说的“非常精确的观察”放在一起来看,就特别有意思。我们看到童先生思考的跨度,从一个非常细的细节,可以到达一个人文主义者超越的状态。
中国当代建筑学与园林之间有如此多的反馈,正是因为童先生那一代人在园林与建筑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桥梁。建筑师会观照园林,反过来园林又给建筑师不断带来重要的启发。建筑与园林之间的连接,无法通过一种细分或专门化的方式达到。只有回到童先生这样人文主义式的思考,才有可能去激发建筑和园林之间连接的活力。刘敦桢先生发明了大量严谨的理论架构,使得园林这个事情可以以当代学术的方式被讨论,这是立学科的工作。而童先生非常像是一个游离者。恰恰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的方式,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补充或是提示了一个大框架之下某种更加微妙、活生生、有创造力的东西。回到人文主义层面,不受限于具体细节的描述,对整体进行观照,这个是我受到的最大启发。”
经由拙政园散步后,下半场讨论以庄慎、柳亦春、张斌等当代建筑师为代表,从实践经验与困惑等方面,分享了他们所理解的园林与中国当代建筑创作的关系。

“对建筑师来说,学习园林或传统建筑空间,特别有启发的不是仅仅学到了什么具体手法,更可能是获得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重点在于‘身在内部如何去感知整体’,比如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在山中,如何感知山?因此,像《东南园墅》这样的著作,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实践者来说都是宝贵的学习资料。
设计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是决定性的。作为当代建筑师,如何建立有特征的思考方式?我自己的体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一阵子对于自己的(中国建筑师)身份,对于有没有个性的思考方式这样的问题,曾经产生过焦虑。但当你逐渐明白自己可以怎样思考,你会安心下来,开始沿着自己的方式实践与研究。这个过程中,学习传统空间文化的原理对于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帮我组成了自己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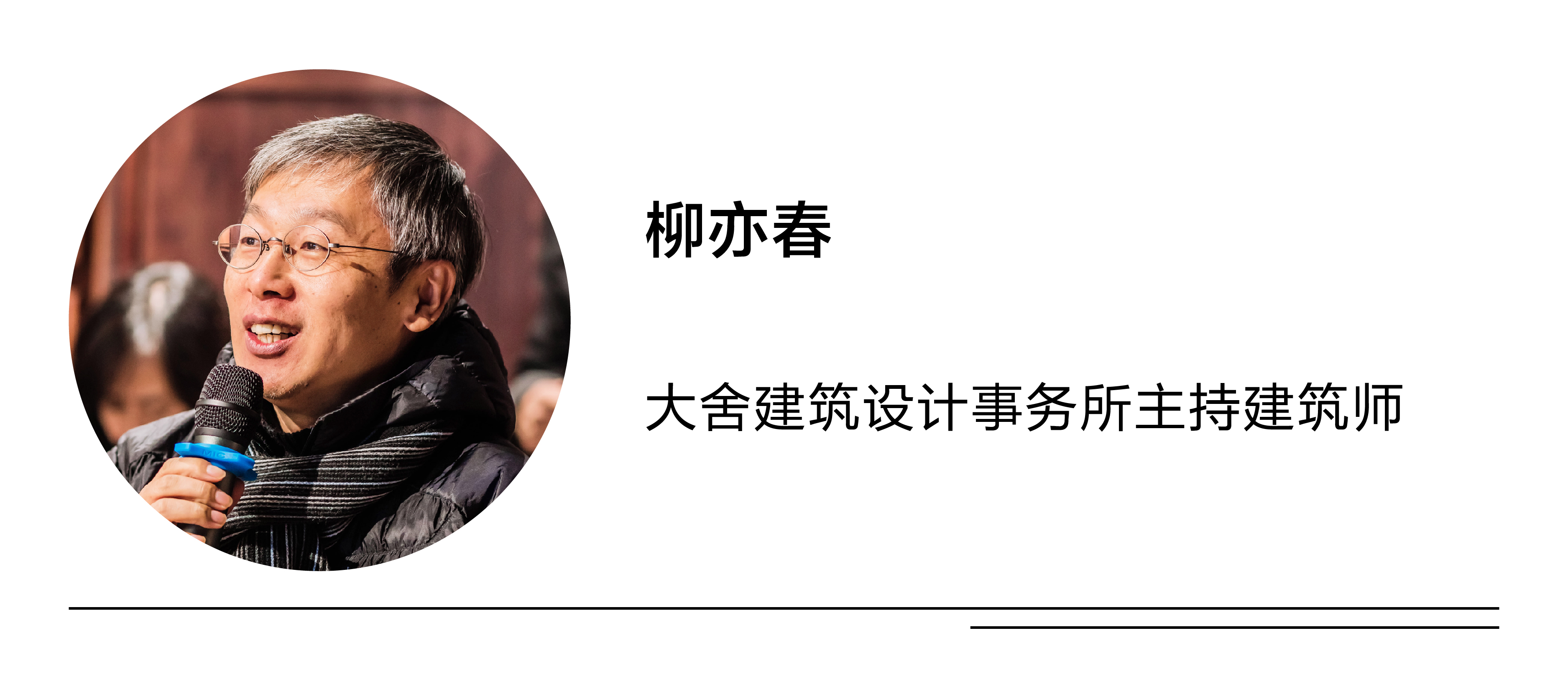
“大舍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和庄慎以及陈屹峰曾考虑把我们定位成具有某种江南身份的建筑师,那时一个具体的方法就是想通过对园林的持续关注来实现这一点。但后来发现这个目标并不是说在设计中用了青砖灰瓦,或者更高级一点用了园林的空间关系来创作就可以达到的,这其实并不是短时间内通过几个作品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后来我们也认识到,越是能够超越那些要素,也许才有可能做到。
在这些年的建筑创作当中,我对园林的关心一直存在,但不像一开始那么急切了,不再试图通过园林里的某一种手法,或者某个理念去达到设计的目标。其实江南园林是在特定的时间与文化当中产生的,是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趋于成熟之后沉淀下来的生活空间形式。今天我们能以什么样的形式去重新呈现?这会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创作,怎样才能超越具体的手法与形式,去筹谋一座当代中国建筑,或是当代的中国园林?童先生在《东南园墅》这本书里说‘唯有文人才能够谋划一座园林’,对今天的中国建筑来说可能也是这样,当然重点可能并非是否还是文人,而是唯有超越作为建筑师的职业身份,令自身具备足够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使其变成一种无形的东西,自然地流露在建筑创作当中,才有可能去设计一栋真正有深度的、展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建筑。
所以我觉得,园林曾是承载中国人智慧、诗意与情趣的载体,或许当代建筑可以超越‘园林’这个空间文化形式,找到一种可以继续承载今天我们关于智慧、诗意与情趣的新形式,这个是我更感兴趣的方面。当然园林里面会有很多具体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营养。这些年随着自身的创作,我越发觉得“因借体宜”的造园思想具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就是说:要能在每一个设计中做到因势利导,去借用一个具体的地点里面有利的东西,让其本身的价值和能量发挥出来,并能够得体合宜,这的确可以成为被继承的建造文化,而不是那些具体的手法和模式。这也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一个创作方向。”

“这么多年,与一群喜欢园林的建筑师为友,大家有非常多的观照和讨论。我个人的体会,更多地是把园林作为反思建筑学的镜像。
建筑学的传统是造物的传统,而园林不是。造园并不是造山、水、树、石、房子,而是建立一个交感的系统,让人与其所处的世界相关联。这个事情确实是建筑学做不到的,建筑学努力做,但到现在都做不到。一旦开始造物,就会陷入物与我的两分,两分之后再去创造,再去讨论物本身的诗意。园林可以达到承载感官与欲望的极致,是心性的神游。这样的物我关系能不能进入建筑学语境?进入了以后还是不是建筑学?
对于人来说,不管在任何文化环境中都要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但是工具不一样。在园林这样的工具背后,体现的是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作为,这是否有进入当代建筑学的可能性,我个人感觉是不太容易,因为两者之间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异。但是看到这样(关于园林与建筑)的思考,以及建筑师如何看待自己职业的局限性,仍然是很关键的问题。”
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转载请联系有方新媒体中心。
139****0030
6年前
回复
183****0100
7年前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