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员王珞丹来到建筑圈,以12期《丹行道》,与12位中国一线建筑师聊了聊天。
一边在银幕上演绎别人的喜怒哀乐,一边却隐身于建筑背后探索自己的空间表达,如果建筑和人都是容器,他们要感受什么?吸纳什么?又将留下些什么?
《丹行道》第4站,广西桂林糖舍里,和董功的一场“见招拆招”。
视频已于10月24日在新浪微博播出,更多精彩于此呈现。

王珞丹 你一直在说“简单”,但这其实是最难的一件事。
董功 对,因为我们说的简单不是没有内容。简单是把所有复杂的问题都理解、化开,然后最后呈现出你的智慧,它靠的是我们自己去凝固出来的那个东西。这里的“简单”不是像一个小孩子不知道过程中的复杂、就直接奔去了的那个状态。艺术作品是经过艺术家转化,作品里有化开再凝固的过程。这个是我所说的“简单”,它适用于所有跟人文相关的领域。
在我们这个社会,人进入复杂不难,因为你会被传授知识、被教育;知道的事越多,我们仿佛就越丰富、愈发有学问。我觉得到了最后那个层次,如果你没法把事情化开,再凝固成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就没达到最终极简单的状态。难就难在最后这一步是没人教你的,也没法从书上看到,完全是靠感悟和修炼。
王珞丹 那么,属于你的简单是什么样的呢?
董功 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做到吧,或者说没有完全做到。
这种程度的敏感,可能很难被外界看到、理解。我大概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东西,我总是会对一个事不满意,也许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在大部分人觉察不到的精微的层次上,但这个层次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可能你之前走的九步,都能通过努力奋斗、不断积累来实现,好像有章可循。但是最后那一步甚至那半步你能不能走得到,这不仅靠努力,还要靠缘分。我觉得这事还挺残酷的:你是不是这块料,有没有那个机缘,会不会获得一个机会,它不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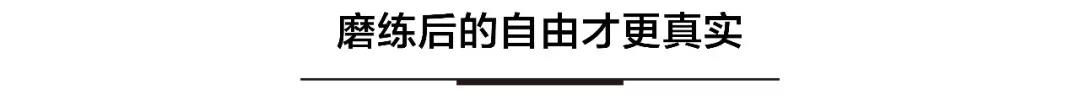
王珞丹 好奇你那前九步是怎么走的?像我,最开始演戏时,一度完全没办法看自己的作品或正视自己的表达,尤其是第一部戏。看了之后,就觉得对自己太不了解了,心里想的和呈现出来的外化表达相距甚远;后来慢慢对自己愈发了解,能删繁就简地去控制好自己的表达,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我修理”的一个过程。你有这样的时候吗?
董功 你说的这个我非常理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前几天,我们事务所一个相对资深的建筑师在“happy hour”给年轻建筑师讲解日常工作规范。听起来这就是一个很繁琐的与人合作和沟通的规范,用来约束事务所内部建筑师的工作方式。我认为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因为首先,从一个事务所的运作角度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到有效;而年轻建筑师们希望实现的都是天马行空的设计,就像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大师”那样,然而事实上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一点自由和所谓才华,只是建筑过程中的冰山一角。建筑背后有着大量的很条理化、很辛苦的东西去支撑它。建筑不是一个瞬间的艺术,不是李白喝高了以后很快就能写首诗。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天天都会想自己为什么要被训练处理这些琐碎的事情,担心内心的才华被这种训练磨掉;而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才华,是怎么磨也磨不掉的。如果哪天你觉得你的才华被磨掉了,那其实是你以前就没有那个才华。
回到你刚才说的话题,我们这个专业需要经历过这些限制,纪律,规范的磨练;但最终到了某个阶段,你又能跳脱出来,那个时候呈现出的某种自由的表达,才是更精准、更真实、更有意义的自由。

王珞丹 这是一个修炼。
董功 而最后能到这个状态的人,少之又少。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在这件事儿上都差不多:人作为一个很大的集体,最后能到那个尖儿上的很少。
建筑师有的时候会需要有意地压制最容易得到的那种美感,会克制这个冲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设计一个房子,不能漂亮得太容易。我觉得这个是共通的,文学、艺术、电影或者表演也一样:到达某种境界时,追求的便不再是一种单纯悦目或者悦耳的美感。
王珞丹 但是在选择的过程中,你决定用什么材料、什么形式表达,这个过程应该挺纠结的吧。一方面是要让每个人在进入或看到建筑的瞬间就感受到它的气质,一方面还要克制自己的表达。在第一眼看到之后还能有所回味的东西,是最高级的。
董功 我觉得伟大的演员和伟大的建筑师最终要面对的事是一样的。把一个东西做漂亮不难。但是你要把一个东西做到有深意、值得回味,就不全是靠技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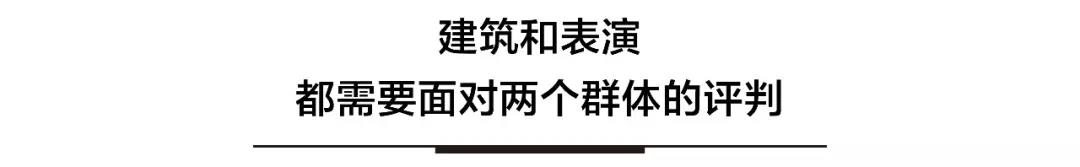
董功 建筑和表演还有个共通之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房子,要同时面对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普通人,包括房子的使用者;另外一个是专业领域的同行。如果把建筑称为一个学科,它里面有很多专业的东西,不能期待所有的人都明白。而建筑师做房子时藏着的很多东西,其实是留给同行看的。
王珞丹 我以前演过一个戏,摒弃了以往观众熟知的我的表达方式去诠释了一个角色。但是观众对此的评价很差:一个以前这么生龙活虎、这么逗趣的女孩子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呆瓜,类似这样;而业内人士跟我聊过那个戏,他们大部分都很喜欢。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比如你自己或者业内人士都很喜欢你的某个建筑,但老百姓不喜欢。因为毕竟是公共建筑,每个人都可以去评价,就像一部电影,谁都可以说两句。
董功 的确会有这种情况。比如你去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觉得还挺酷的,但是如果那是你家,你可能就会拒绝了。就像在船长之家的项目中,这家一共有四口人,船长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儿子。在房子盖完他们一块走进去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船长的表情,他一直是面无表情、甚至有点木的状态。然后他问我,咱们这个做完了吗?我说完了。他说腻子不抹了?我说不抹了。看得出他不太能接受混凝土光秃秃的墙面,感觉像是住在一个未完工的房子里。
王珞丹 但是他女儿喜欢吗?
董功 女儿很喜欢。他女儿是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的,一个很新派的女孩,最后其实是女儿影响了父母。现在过了快两年,他们都很喜欢,很多去到他们家的人都觉得这个房子很棒,他们也觉得自豪。我举这个例子其实是想说,比起电影来,建筑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在一个很小的专业圈子里互动的,所谓媒体的覆盖度也都是在这个范围里,真正作为用户层面的老百姓其实在这种互动和交流范围之外。建筑不像电影或者表演,会引起那么多的公共讨论。我觉得这是这两个行业的区别。
我经常做的一个比喻就是:建筑和武功有点像,比如说给老百姓、观众看的,就是我拉了一个架势一拳把他打倒,这事儿观众一鼓掌就行了。如果建筑能把人感动了,可能他们说不清那一刻的感受,但其实就是达到了武功里一拳击倒的效果。但建筑还是一门学科,好的建筑要有学科的价值,要有对学科的延展,这是建筑师要同时面对的。我前段时间去了几次佛光寺,一处唐代的木构,在现场能觉察到很多当时古人在建造时的玄机。虽然相隔一千多年,但建筑作为一种物化的智慧,好像一直就在那儿,永远都不会被时间磨灭。这又有一点儿像武功里面高手之间的“见招拆招”了。



王珞丹 高手对决听起来蛮有趣的。但你不知道,我妈看我演的戏,电视剧从头开始看,看完第一第二集的时候就经常说,“哎呀你这没有进入状态啊”。我说是吗?她说“但是往后看到第六集我觉得你这个人物对”。我就默默乐了。因为我妈一开始觉得人物状态不对,是因为需要有一个代入感,得有一个前面的铺垫。我妈都看了我这么多年的戏了还在问我同样的问题、觉得越往后越好,就开始探讨表演的问题;我每次都要跟我妈不厌其烦地解释:“妈妈,我们是跳拍的,第六集最先拍的”。
董功 建筑也是同样的。有的时候,你还不能让建筑最好的东西发生在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人走入一个建筑里面是需要时间的,不像看一张画,它一下就呈现在面前。感受建筑需要一个穿越于其中的过程,这一点很像电影。空间体验中最高潮的地方一定是被建筑师控制住的:比如从一开始如何去铺垫,到最后那个空间以后,怎么让人能够达到一个情绪的合适点......建筑里面是有一套时间线索的。


王珞丹 建筑里也会有一套时间的线索?
董功 对啊,人的行动路线可以被理解为建筑中的时间线索之一吧。从某种程度上讲,建筑和电影是有类似的地方。
王珞丹 这么说,建筑师真的有点像导演。
董功 对,所以我们建筑师也会经常谈比如说剪切、剪辑,怎么去控制一些空间,最后要呈现的状态是什么,也有类似导演的这套东西。只不过它是用一个更抽象的方式呈现,没有电影那么直接。在建筑里面,这个潜在的路线是建筑师埋在那里的,它是建筑师埋在里面的一个基因。当然,建筑师也不一定能让所有的人都按照你的思路走,这又是它跟电影的不同之处,对于电影来讲,大家都会按照同样的时间线索来观看。
我这次去威尼斯,又去了旁边的帕多瓦( Padova )看帕拉第奥( Palladio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对专业的建筑人来说,当自己的状态不一样时,面对同一个好的建筑,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已经去过很多次,每次理解到建筑师在他那个历史时间点埋进去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当我还是一个学建筑的学生,我什么也看不出来;当我有一定经验或自己的感悟,到了能看见它的阶段,就能感觉到原来还有某种东西在里面——你能很明确地知道,这些是建筑师深思熟虑过后留下的,而不是偶然。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简单”。我觉得电影也是,文学也是,它们藏着一层一层的东西,不要求每个人都能看得懂。但如果你能一层一层吃到比较深,你就会体会到这其中的智慧……

……

版权声明:本文由王珞丹工作室、直向建筑授权有方发布,欢迎转发,禁止转载。
投稿邮箱:media@archiposition.com
上一篇:SHL新作:新西兰基督城中央图书馆落成开幕
下一篇:有方报道 | 罗杰斯40年后再谈“蓬皮杜”:当年很不受欢迎,得知我是它的建筑师时,一位女士用雨伞攻击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