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有方“建筑师在做什么”第128个采访。
张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建筑光学专家。在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在张昕看来,照明设计需要有更多研究性的举措;如果没有用户的反馈数据,照明设计师的许多做法,仅仅是一厢情愿。
当下,人们对照明设计的了解仍不全面,对其在建筑设计中的介入方式也知之甚少。如果把天然光设计也作为照明设计的一部分,它将贯穿于建筑设计的始终。建筑师在方案早期就会考虑用光,照明设计师从概念阶段就可以介入,很多设计因为光的想法而改变空间布局、构造做法;到了实施阶段,设备的调试、应变或纠错等操作,是最为“较劲”的照明设计工作。
我最近在做的项目,以与建筑师合作,带有探索性质的小项目为主,大而复杂的项目则是位于首钢的冬奥组委办公区等。与过去相比,增加了与实证研究结合的健康照明项目,得到地产企业、养老机构的支持,这类项目需要引入被试进行实验居住,根据生理、心理数据修正照明设计,同时进行标准制定和论文输出,并最终交付给真实用户。
近期最有收获的项目是故宫雕塑馆(慈宁宫)的照明设计。项目负责人冯崇利和合作者周錬老师,一位是雕塑家,一位是雕塑科班出身的著名照明设计师,他们都专注于结构完整和细节完美,做事不计时间和精力成本,帮我改掉了一些“油腻腻”的设计习惯——项目做多了之后,设计师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捷径,看见熟悉的桥段、节点或者喜好后会自然地使出套路化设计。然而,这样的思考方式不够一手,失去了探索新的设计可能性的很多机会。要学会拒绝“油腻”,强迫自己在每个地方做出不一样的设计,多走“弯路”,走远路,走耗时间的路,这些都是让自己进步的特别关键的东西。



在理想的状态下,我希望可以设计一个持有“倾听”状态,可被用户改变的照明设计——如果是城市的夜晚,市民不同就该有不同的面貌;如果是养老院,每个老人的卧室照明都应该是他/她最喜爱的样子。
当下,日常的设计都可以实现用户调光,但用户只是凭视觉感受去调光,而无法关联视觉之外的事情。我希望从“骨子里”建立起房间的光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基于个体的健康或舒适去调节。比如,很多人知道在暗环境里看手机对眼睛不好,但常常由眼睛的疲劳感驱使自己被动的调节照明,如何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在系统上将光线自动调节到更适合这个人的状态——而非基于眼睛判断和不健康的喜好——这是可以深入研究的事情。


养老,是我最近很关注的一个社会议题。前段时间,我带着学生在养老院针对80岁以上的志愿者做全周期的行为观察和光学测量,体验了高龄老人的群居生活,充分感受到单一学科体系的贡献十分有限。相比高校里流行的抢占话语权式的科研组织思路,“抓紧时间贡献对别的学科有用的新知识”对解决问题更为有效。
在养老院的照明议题上,作为设计师的我们面临许多困难。设计师都是相对年轻的人,而人眼处于不断衰变的进程中,我们没有办法基于自己的感受去判断老年人到底看到的是什么。如何面对一个不确定的、衰减的“未来”去做设计,如何提供老年人表达的机会,获取“合适”的主观反馈数据和生理数据?要从研究的角度切入,依靠模拟、实证的方法,通过寻证的方式反推,而不能简单地基于常识或中年人的想法去设计。

……
有方 与过去相比,照明设计近年来有了哪些变化?
张昕 跟十五年或二十年前相比,建筑师、业主等越来越认可职业照明设计的价值;照明设计团队在数量上增长很快。以前大家关注更多的是视觉功效——能不能看清楚,之后是好不好看。现在会关注更多的维度,比如人在空间中是否健康,是否容易入睡。
遗憾的是,尽管在设计上有了蓬勃的发展,建筑光学的研究规模和水准,并没有明显的进步。在现有的人口基数下,照明产业的研究缺口很大。其他的比如照明设计评论,似乎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成体系地评价照明设计。
有方 如何看待研究与设计之间的关系?
张昕 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做设计的人跟做研究的人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我一直不建议“只做设计”或“只做研究”。当有项目在设计和研究上都具备条件时,我会把二者“捏”到一块儿。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获得用户反馈数据,如果没有反馈数据,所有的调整都是设计师的一厢情愿。
我一半的精力是在做研究,重点是天然光环境的非视觉效应。眼部进光跟人的睡眠质量等生理节律相关,比如白天一直在户外工作的人,眼部进光量多,充分抑制褪黑激素分泌,晚上就更容易入睡。以前,这类研究只在实验室进行,脱离了真实空间和真实生活情境。最近,我们在办公、住宅、养老的实验项目里进行尝试,获取生理数据以及其他反馈,从健康的角度去评价何为更好的光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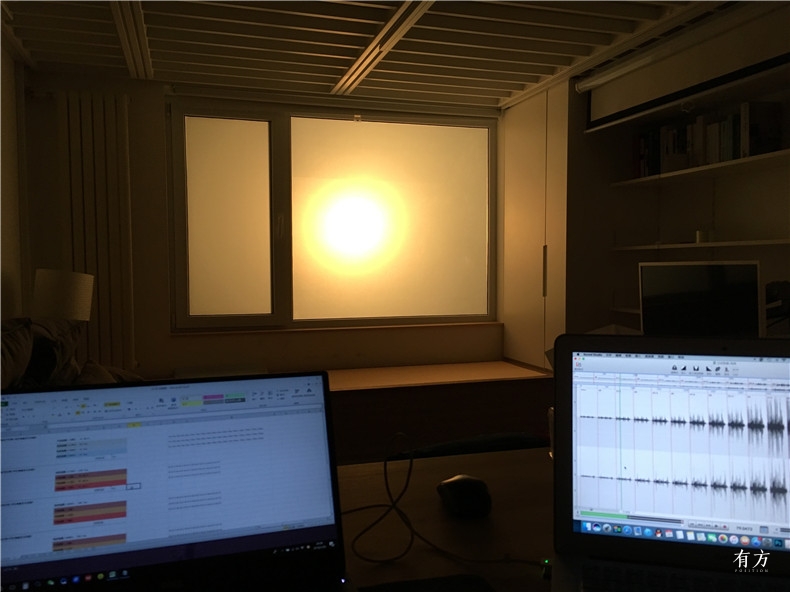



有方 哪个项目留下的遗憾让您最为印象深刻?
张昕 因为图纸无法准确表达光影,照明设计的遗憾多指完工结果与不为他人明确知晓的心理预期之间的差距。很难碰到完工照片长得不像当初效果图的建筑,但光的遗憾都长在“脸”上,直接接受群众的检阅,不同于节能、声学等只被专业检测审视。当然,空间被照亮的喜悦会冲淡那些遗憾,所以很多时候遗憾是被深埋的。照明的实施在最后,管控的话语权不够,因此一个照明设计方案的抗风险能力很重要。在没有专业管控的项目中,一不留神,“突然发生”的图纸变革、预算超支、工期压缩等都能带来遗憾。
有方 在职业生涯里,有没有对设计这件事情失望过?
张昕 从未。
有方 如果不做建筑师,您的理想职业是什么?谈谈自己对这个理想职业的设想。
张昕 我的职业是教师,岗位类型是教研系列,即必须兼顾教学与科研。在建筑科学里,科研又分为实证型的研究和研究型的设计,三件事在学术上关联,但工作内容和思考方法各异,三者彼此互补,互为调剂,已经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职业了。
有方 在未实现的设计里,哪一个让您觉得最可惜?
张昕 我有次一时兴起,画过一张什刹海的夜间意向图。虽然它不是一个真实发生的设计,但我每到什刹海,都会感到可惜。因为暗是照明设计的一部分,最可惜的是,那些本该暗的部分被照亮了。
在公众的认知里,照明设计就是把黑的地方弄亮。但对于做照明设计的人来说,把空间弄亮是最容易的事情。若在弄亮的过程中有节制地保留暗,则非常考验“功力”。不美的东西在暗的时候比亮的时候总要好看一些。另外,暗与文脉相关,弄亮会削减其文化属性,比如在乡村、园林里的照明设计,如果弄得跟万达广场一样,那肯定有问题。我认为,理解暗的价值,把它作为特别值得珍视的内容去对待,是区分照明设计师的关键点之一。



有方 当前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打算如何解决它?
张昕 设计师与老百姓,甚至设计师之间,喜好和品质判断的差异巨大。即使是自己的父母,每次问道“这个(这么漂亮)是不是你设计的?”,多半会看见电视里播放的正是自己极力反对的设计。这个用说教解决不了,喜好是自由的,只能做自己坚信的设计,争取影响到路过这个设计的人。
有方 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他(她)在建筑和光设计上对您有哪些影响?
张昕 我有很多老师。詹庆旋先生是我的导师,一身旧时代学者的严谨和不妥协,似无形的人格铁箱。周錬先生一辈子在美国开业,像是钥匙,专教如何解放思想地去设计。金鹰先生专攻城市模型,很感激他把英式的科研思维嫁接给我。
有方 最近读的有趣的书是什么?简单阐述理由。
张昕 学语文和数学教材(三年级),目前唯一的,也是不能马虎的“课外阅读”。其中乐趣当然不在于指导检查作业,而在于唤醒记忆,一道题、一道题的小时候。
有方 最近的一次旅行去了哪里?旅行对您的设计有何意义?
张昕 去了一趟固安,其意义跟去学校踢场球也差不多,除了放空还是放空,脑子装满了就不转了。
有方 您认为什么会改变未来的建筑?又如何看待建筑学的未来?
张昕 虚拟现实+脑科学+物联网,将实现认知与反馈的闭环。电影《头号玩家》呈现了虚拟空间带来的“真切”美好,建筑则沦为随意堆积的箱体,只剩下保障身体隐私和为虚拟设备防雨、供电的功能。借用电影的片尾,建筑学的未来也许在于如何防止真实生活被集装,用真实的美好战胜“真切”的美好吧。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图片由建筑师提供。转载请通过邮件或电话与有方新媒体中心取得授权。
上一篇:红砖的现代转身:小径湾大学 / Foster + Partners,GDI
下一篇:雷宅:工匠建筑学与数字乡村 / 张雷联合建筑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