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9日晚,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迎来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及理论教授——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他以“‘巨型’作为城市景观”(Megaform as urban landscape)为题讨论了更具中国城市尺度和混乱城市发展背景下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创作态度和方式:MEGAFORM。此文由有方青年作者、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讲师、再造建筑事务所创始主持人赵德利撰写,作者对弗兰姆普敦提出的“巨型”概念进行了梳理与解读,并把其置于王澍的日常城市 \ 建筑实践中,从而促成了两者的一种“历史性对话”。

—— 写于“‘巨型’作为城市景观”之后
当弗兰姆普敦及其好友——同样身为建筑历史与理论界的重要贡献者—— Gevork Hartoonian 在香港大学和中国美院讲座上放映王澍的建筑作品:水岸山居和文村——作为特定文化领域的建筑创作启发全球文化领域的建筑实践的一个范例,我并不觉得奇怪。
王澍上世纪90年代的个人建筑探索建立起了他和弗兰姆普敦在当下的历史性对话:他试图在快速城市建设进程中,追寻建筑本质的孤独思考与实践和弗兰姆普敦的“一种抵抗的建筑学”在那个历史瞬间走到了同一个交叉点。
伴随着王澍当下作品所贡献的新的社会、文化动力,这种回味和感概显得弥足珍贵。此刻共通的“抵抗建筑学”的效果是没有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并成为不同个体间相互吸引、走到一起的“神秘力量”:在弗兰姆普敦的国美讲座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原来“巨型”理念内核和国美建筑学人——王澍的日常城市 \ 建筑实践分享着多么同步的追求和意图;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持续思想其实在其它文化领域也在以不同的形式发生着。

这时,“批判性地域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不再是面对一种固定可以保证成功的建筑发展套路,而是不同个体在流动现实碎片的个人持续体悟、抵抗与批判性的实验下,再创造出的新现实之间的持续交互与碰撞体系(建筑评论)。而这样的新建筑不会受到历史先例的限定,并在理解历史的视野下,成为新的历史。与弗兰姆普敦聊到这点时,他还没等我说完,就已经帮我说出了突破历史先例的可能性:
城市元素在不同资本运作和权利机构的代言下,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拼贴,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整体、连续性的设计已经不太可能。在此,建筑师需要在接受现状——城市混乱的现实和碎片化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不妥协地坚持尝试、调停,在充满了限制的已有城市时空中,去衔接、转变、结合城市的地景、空间的多重破碎维度和空间脉络现状,创建不同城市事件可以彼此协作互助的新兴建筑系统。
我把这种与现实城市碎片同样破碎的内在及潜在互通关系的挖掘(新关系),以及对它们协作互助的新物质模式意义的建构叫做:一种携带着批判地域识别性的明确建筑可能的“前-建构”。既然如此,在可以“建构”之前,衔接转换现实碎片的空间新关系成为必由之路。每一次建筑设计或建筑思考实际上都是在新建筑中寻找新的意义。这种“新”并非绝对之新,而是相对于过去空间生活在面对外力介入时建筑师所关注的转化和转变。在新建筑出现之前这些新意义和形式不曾存在过。要么重复要么再造,这是每个建筑师要去思考的。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用最柔和或自然的物质、空间、生活、行为、接口的介入来重塑新的现实。这时的建筑新意义带来的我们熟知的建构机会甚至有机会与目前的资本及权利体系相适应、兼容,即便不可以,我们也知道还有哪些建构点是有待提高或不能实现的,继而进行建筑偏离时的灵活调试-实验性的建筑作品。
不幸的是,当代建筑实践的主流是基于某种共通的预设,建构自以为多样却实为一致的建筑物体。建筑在此不停的被扭曲和意淫——讲各种各样的多愁善感的故事。建筑师在探讨建筑元素或所谓的空间之时,是否在真正意义上探讨建筑的本体?我保持怀疑。在我看来,现代主义建筑的危机不是建筑的危机,那些细部、技术、工业化批量生产蕴藏着非凡的建筑效果和建筑潜能,可人们创作建筑的内心却更多的停留在了这些现代“建筑进步”的通用和匀质层面之上,或者“枯燥”的预设没有能力驱动这些现代性的潜能。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现代建筑的危机发生在建筑师对自己角色和工作本质的不解和放弃自治探索之上?
相对于把 MEGAFORM 翻译成“巨构”,王澍更愿意把它翻译成“巨型”——以指代每次面对不同时空领域,建筑师都勇敢地在原型中再创造新的建筑型。并且“巨构”会引起误导,别人会以为是 Megastructure,同时,“巨构”表达的也是一种风格和特定尺度形式结果的建筑效能表现。而弗兰姆普敦想表达的更多是一种不受风格和样式限定的、动态的、每一次面对不同场地的不同创作——即带有多元空间接口特征的、独一无二的建筑发明及设计方式。弗兰姆普敦在他的《巨型作为城市景观》(Megaform as urban landscape)中解读了 Megaform 和 Megastructure 的区别和关系,他认为 MEGAFORM 注重内在空间秩序和形式织体的全局整体,并不必要去凸显结构的表现,看上去似乎会多少表现出 Megastructure 的形式特征,但又不会拘泥于此。弗兰姆普敦期望“巨型”的实践,可以在充斥着大马路和图像消费的破碎城市现实中,去再造可以衔接转换这些碎片的批判性场所与新型城市地标,在新兴的城市生活中寻找并打造人性和生活的本真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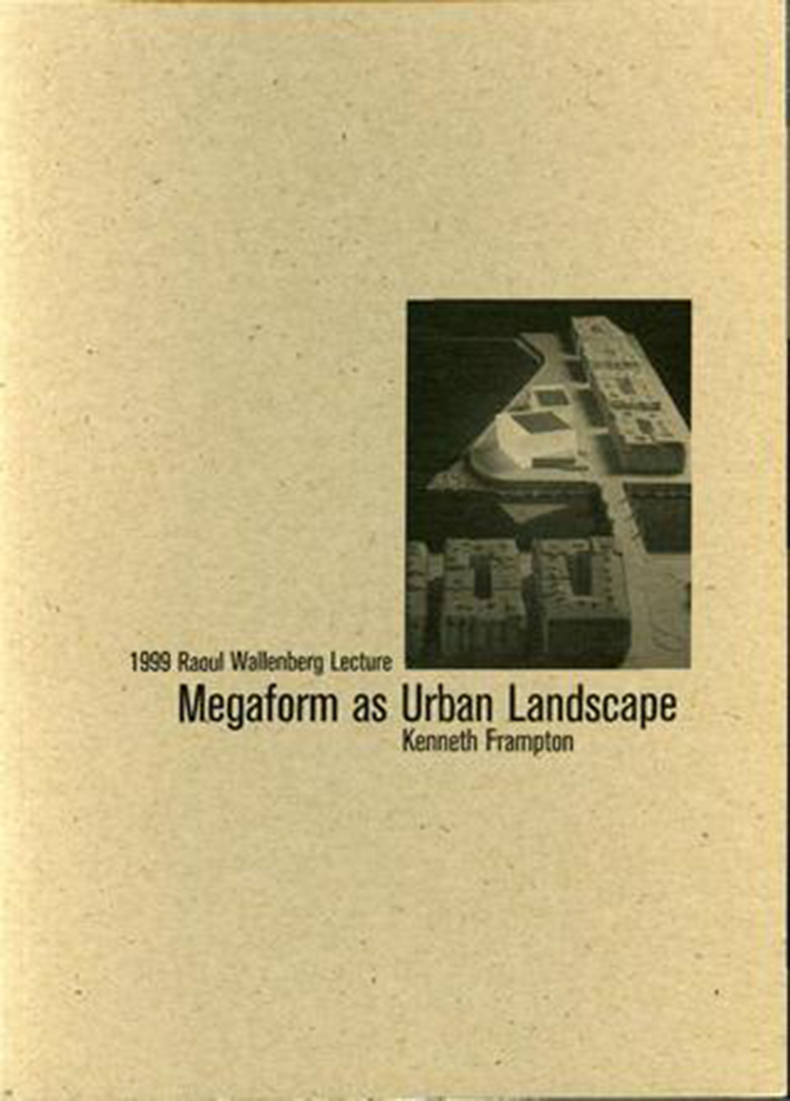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巨型”的设计思想语境中,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其实是一回事。“巨型”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动态的与破碎城市发展持续相对的文化及社会性的生产力,为建筑具有自主意识形态提供了精准工作的内容与接口。这并非历史上对社会精神的研习后对其的赋形支持,而是致力于时刻与正在发生的现实进行相互促进的对话。
相对于创建一种孤立和封闭的建筑物,“巨型”试图从空间层面,在现有混乱城市大系统中去建立可以嵌入这个大系统又可以独立自主运作的新景观领域。人的城市生活,和其它城市元素的互动在建筑的自主性下可以适应不同城市碎片之间新型协作与互通。弗兰姆普敦最早是从 Rafael Moneo & Manuel de Sola Morales 在1992年设计 L’Illa Block 中获取到“巨型”的灵感。

在这个项目中他读到了建筑如何作为一种水平的、从内到外都在和城市互动的空间系统,一方面具有城市的识别性(起伏的屋面),一方面又是坚实的建筑实体(可穿梭、可停留),时刻在处理和转换不同的城市剧情:从楼下的商业界面到上层的居住空间,再到他们向其他城市区块的可达性延伸,试图在当时混乱的巴塞罗那城市发展区块建立清晰和流畅的城市多重功能的互助关系。
在这一灵感的驱使下,他开始找寻历史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巨型”实践,以期更为全面、细致地为我们解读他的城市观察和实践可能,包括巴黎旧王宫新奥尔良廊(Galerie d’Orleans Palais Royale,Percier & Fontaine,1829);1929年在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弗罗茨瓦夫)地区进行的住宅展中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的作品;1930年柯布为阿尔及利亚做的城市规划;再到距离我们更近的2002年,FOA设计的横滨大栈桥国际客运航站,等项目的解析。



各种地域都有着特有的社会问题、城市问题,并时刻处于权力、资本与建筑活动的纠缠之中:一方面是建筑师想去再造现实的内心意愿;一方面是作为商品的建筑模式的阻挠。这时,建筑活动自然地、自发地、本能地会去抵抗,抵抗当时当地的权力或资本的欲望,以及变革或争端所需要的建筑模式。
那么,是否结束了这种带来抵抗的建筑模式,就能够实现大家的理想建筑?遗憾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的消费主义文化迅猛扩张到现在的全面普及,这种套路建筑的发生方式还看不到任何结束的可能。另外,没有建筑师和权力机构或资本的“对谈”,也不会催生促进新的社会、文化动力的新建筑。这时建筑的定义转换为这种持续的双方交流所产生的社会贡献。
相反,在探寻建筑不属于谁或谁的权力的想象解答过程中,自治,成为一种既不是大师(权威)也不替代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的方式,而是在与其对话(抵抗)的力量发展的高度进步视野中,通过对它产生的现实碎片及文化效果的非常精细的“前-建构”的方法来“再造”它。(注:改写自 Pier V Aureli 的The Project of Autonomy: Politics and Architecture within and against Capitalism 中的:“自治成为一种既不是大师也不是抵抗资本主义的方式,而是在与其对立的力量发展的高度进步视野中,通过对它的文化效果的非常精细的解释学的方法来转化它。”,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2008。)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建筑如何作为一个个人在广博社会领域所追求的建筑自治体所抵抗或调停的城市元素,而非一种源于哪些理论或社会意图的建筑结果。否则,建筑将非常容易受到道德、民主、媒体、科技、权威、潮流等力量的绑架,成为一种建筑师心中共通的,理所当然的实践动力。这时,无论建筑师做出了多少建构的花样,使用了哪些新的科技,本质都还是千篇一律的作为物体的建筑。这完全不同于每个个体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内心的真实追求去探索自己的建筑学。以王澍为例,他的乡村调研和他对当代建筑实践的关注点紧密关联,这是他在历史上的探究过程中自发涉猎或触摸的知识领域,而非追随某种社会潮流的共识。即便设想一种极端的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停滞,另一种相互的抵抗注定是没有结束的坚持。
在 Michael Hays 评析意大利建筑史家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的资本主义建筑批判时谈到建筑步入的两难境地:建筑在资本主义下不可避免地以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形式重复社会的结构。一旦建筑抵抗,资本就会从服务中撤销它,不让它执行。
这时,建筑学的定义不再是任何建筑物体性的效能表现或建成与否,而是在建筑师试图发掘有着自主意识形态的建筑的抵抗过程中所产生的新建筑思想,新文化及社会动力。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建筑,建筑效果的概念及实践成效是没有必然保证的,同时这样的建筑所呈现的不可削减的效果也是历史和社会境况的一种珍贵样本。
面对各个年代都有的建筑的困境和限定,塔夫里在上世纪70年代指出20世纪先锋主义的挑战:减少艺术体验的结构以便到达一种纯物体的状态;折衷主义;使用资本主义城市已有的视觉符号;快速的组织和改变;交流和使用的快节奏与趋同性等。至此,建筑理论踊跃地迸发,因为有一类建筑师不想轻易向被“谁”指定的建筑定义妥协,他们也不会因为没有项目而停下建筑的思考与实践,建筑进入“讨论(Discourse)”的状态。我并不想在这里谈太多“建筑讨论(Architectural Discourse)”的全面建筑学“贡献”,但其中一条就是建筑师与现实的远离和建筑社会意义及必要性的缺失。

上世纪70年代,一批有理论研究倾向的建筑师以及从欧洲前往美国的“被驱逐者”借由 OPPOSITIONS 杂志发声,成为当代建筑文化的代表,其中包括:埃森曼、库哈斯、罗西、文丘里、盖里、菲利普·约翰逊、伯纳德·屈米、迈克·格雷夫斯、理查德·迈耶、肯尼斯·弗兰姆普敦以及曼弗雷多·塔夫里。
所以,我们后来会看到柯林·罗将建筑的先锋行为定义为建筑向形式的依附——“Physique Flesh”;到彼得·艾森曼排除建筑的现实背景,用纯形式元素的变形和组织变换进行衍生操作所带来的不顾及其它的,被打折的建筑的自治与抵抗;再到阿尔多·罗西通过集群的建筑理解所提取的城市模拟物的建筑类型探索……然而,当时这些建筑师并不知道自己的抵抗会带来怎样的建筑效果?他们不会想到,他们的阶段性探索居然成了更广泛人群的建筑意识形态的复制范本!此刻,建筑的现实意义并未有所增强,建筑成为了一种创作的目标,而非一种可以协调不同城市和文化发展动力的动态的设计伦理:一种在不同时空,场地上,每次都需要发掘不同建筑的自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缺失的。
这也是我们如何理解“批判性”这个词的基础和意图,我们不想用一种建筑的教条去步入即将发生的现实。这一点也是弗兰姆普敦在1983年发表的“朝向批判性地域主义:一种抵抗的建筑学的六点”中致力于去解答的。建筑怎样才能携带建筑时代的技艺同时,又能保持和表达其地域识别性的意义。弗兰姆普敦在第三条“批判性地域主义和世界文化”中讨论了批判性地域主义提出者:希腊学者亚历克斯·佐尼斯(Alex Tzonis) 和丽莲·勒斐芙(Liliane Lefaivre)对于地域主义的模糊性的警示:批判性地域主义自有限制,平民主义运动的兴起是种地域主义的更为老套的形式,揭露出地域主义的若干弱点。没有新的建筑可以在顶端控制下,在缺乏新的设计师与用户关系的条件下涌现。
这暗指两种基本的抵抗:一种是地域性建筑在全球化的吞噬下如何继续存在,自我保护,实属不必要创造新建筑的对已有建筑成就的保护;另一种是,在更为广泛的实践领域——任何地域都是地域的认知下,如何去创造新的建筑的同时又兼顾建筑自身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自身特质与识别性。
当弗兰姆普敦继而发展“批判性的地域主义”及其对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抵抗时,当他同时给出如何去实践的具体方式——建构时,大家似乎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因为这样的建筑意识好像既有现实意义,又链接起了建筑的纯粹核心要素:形式、地域、文化、技艺、科技、事件在不同建筑师的组织下的协同参与。而且也会经常听到建筑师们在讨论建筑的建构如何在表现建筑的本体(如果说建筑的本体是探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尊重了材料的特性并能打造出创新性的交接,又在独特文化背景提供了同样独到的空间体系,我们似乎看到了建筑的胜利。不过请先等一等,这样的建构抵抗的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吗?抵抗的是它的动态发展吗?还是说一方面说抵抗上述现实,但仅限说出来,而建构实践是自我屏蔽和远离这些现实的?还是将其简化为不需要被时刻面对的一种保险的实践方式,只要建构就在抵抗了?只要不去理睬抵抗的外力的表现去做地域性的建构本身就可以了?
在讲座第二天与弗兰姆普敦的好友 Gevork Hartoonian 的聊天中,我们聊到了一种共识,他对抵抗的立场是:
先去“接受”资本主义的建筑现状,再勇敢的把自己扔进去摸爬滚打,寻找调停和谈判的建筑发明,而非彼此疏远去打造一种所谓的理想建筑。
这就像那些说自然多么纯净和不可触碰的想法一样——永远都不会有真实的和自然的新关系的建立,只能远远的眺望。抵抗并不等同于不顾现实的逃避所带来的新兴实践空间。从思想到操作策略都好像十分正确的建构文化在“批判性地域主义”的遮蔽下,逐渐被解读和实践成了用材料的本性所发展的地域性交接就可以讨论建筑学的全部危机。有时甚至以建筑是否“建构了”为评判一个建筑作品的重要乃至唯一标准。相信建筑建构被弗兰姆普敦发展的初衷并不包含获取一种墨守陈规的、只要用了地域性的材料去进行可以实现事件空间的创造性交接就实现了建筑理想的操作法。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两种完全不同的实践态度:一种是先锋主义,另一种是先锋意识。前者的先锋已被标签化、行政化和模式化,即为了谁做设计、用了什么手法、思考了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是先锋的;后者则是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碎片中,发自内心的持续思想,并纯粹和持续地进行创作来追寻源于现实并有能力可以与现实互动和对谈的自治性建筑发明。
如果我们认定我们已经获取了一种安全而又可靠的设计思想,建筑创作即会趋于忽视持续流动和转变的现实,这时我们对建筑的审视不再基于建筑是否为了建构更美好世界的前瞻性的效果,而是根据不同的现代性的理解的已有成就中,去迎合那种建筑思想的需求。建筑及其形式将会提升到没有外在感知、缘由或社会视野的自身语言!
相信弗兰姆普敦并不想一方面追寻抵抗的建筑,一方面却又获取了不顾建筑外部现实的地域性建构,即是抵抗的套路性建筑结果的操作认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建构如何实现自身文化领域的创造性建构结果,而是缺失了如何在可以使用“建构”之前来实现可以对谈那个领域的建筑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前-建构”及其过程。相信弗兰姆普敦自身也感觉到了这种建构文化的限制,这时,他的“巨型”出现了!
不同文化领域在不同年代,面对生发出不同抵抗力的建筑外在“动力”,会给出面向全球的批判性地域实践的范例。这样的实践过程和效果已经超出了作品的结果性与材料交接及其工艺的问题(当然作为建筑师实现理想的建构技艺是基本和必须的……),重点也不是它们继而在一起所被建筑师所创建起来的事件空间织体,而是源于特定地方的建筑学所迸发的创造性效果是可以穿透不同文化领域的界限进行互通和传递并不可消减的。“巨型”作为一种抵抗的建筑学,来自于有着抵抗意识的一个或一类建筑师,这预示着,每个建筑师个体的不同抵抗潜能,和他们自己的那种抵抗的建筑学。
在我看来,相对于说全球化在消减地方还不如说地方会贡献另一种更好的全球化,而这时的全球化不是一种破坏性的结果与过程,更多是不同个体、地域思想相互碰撞和促进的一个动态的对话过程,时刻产生新的地域、新的全球!
参考资料
1.Kenneth Frampton, Megaform as Urban Landscape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Plym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2009, Printed in 2010.
2.Michael Hays, Architecture’s Desire, Reading the Late Avant-Garde, MIT Press, 2010.
3.Manfredo Tafuri, Toward a Critique of Architectural Ideology, reprinted in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MIT Press, 1998.
4.Kenneth Frampton, 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in The Anti - 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 Culture,ed. Hal Foster, Bay Press, 1983.
5.Peter Burger,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trans. Michael Shaw,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作者 赵德利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转载请通过邮件或电话与有方新媒体中心取得授权。
上一篇:朱亦民:荷兰文化的特殊性与荷兰现代建筑的发展
下一篇:深圳没文化?给你一个“打脸”的机会 | 张永和、刘小东、胡如珊、许知远“尚上讲堂”今夏开讲|尚上讲堂第二期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