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正如,建筑师走访城市和建筑之时,习惯通过空间认知来画地图/平面图一样;也许,建筑师看电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自觉的绘制地图/平面图的过程。任何电影镜头在建筑师的眼里都指向一种渴望,一种试图对电影中的虚拟空间进行真实认知的渴望。柏林工业大学建筑学在读博士刘泉泉撰写本文,通过分析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取镜中的空间特点,从场景设置到人物位置,以及窗、镜面对于空间的影响等方面,细致呈现了安东尼奥尼镜头中对于空间的关注,“物理空间某种程度上成为镜头捕捉和表达的一个重点”。本文由作者刘泉泉授权有方发表,文章作者享有版权及最终解释权。
建筑师之眼
正如,建筑师走访城市和建筑之时,习惯通过空间认知来画地图/平面图一样;也许,建筑师看电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自觉的绘制地图/平面图的过程。无论是几个长镜头,还是通过蒙太奇式的拼贴仍可在头脑中实现空间“完形”的几组镜头,在建筑师的眼里都指向一种渴望,一种试图对电影中的虚拟空间进行真实认知的渴望。这种渴望已经被多次践行过,比如Juhani Pallasmaa根据希区柯克的影片绘制的建筑平面图。平面图是起点,当然还可绘制剖面、立面。
而根据这些镜头所呈现的“运动-影像”(movement-image),纵使很多时候无法使人清晰的、完整的、正确的勾勒出(建筑师所渴望的)图纸,却也必然的带来一种深刻的观影的快感,一种以管窥豹式的——或者可说是偷窥般的——对“画外”(out-of-field)的无尽想象。仅仅是片段式的一瞥,便将观众引向无尽辽阔的“不可见”空间!
那些吸引我的镜头,往往呈现了全景式的物理空间,或者说,能够使我想象一个无穷丰富空间。
有些伟大导演的镜头运用方式,显然不在此列,这让我一开始会有点儿难以入戏。比如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比如布列松(Robert Bresson)。虽然二人作品各有其特色,但在有一点上似乎是共性,他们二人都不关注对物理空间的刻画,也许准确的说,是不屑于。德莱叶的电影被德勒兹称为“(空间)深度的缺失,或是(空间)维度的遏制”。以特写镜头著称的《圣女贞德蒙难记》(1928)是如此。尽管从理论上说,特写镜头可以凭借某种方式来表达景深和空间维度,但德莱叶没有这样做,他将人物特写的背景设为黑白,取消了所谓“氛围”维度,但却制造出时间性和精神性的维度(见德勒兹《电影1:运动-影像》)。再以《词语》(Ordet,1955)为例,尽管片中运用了大量的很长的长镜头来交代室内的环境,但是室内空间是极浅的、扁平如画卷般的,那些带有宗教意味、却又抽离物质性的场景并非意在营造一个趋向“真实”而丰富的空间氛围,而在于提供能够串联起一个个特写式的人物的背景,创造精神上的“维度”。(图1-2)。光打在人物身上,环境只是映衬。至于布列松,干脆不用长镜头,连环境都不屑于刻意交代,镜头中所出现的场所、环境都只是人物动作、神态的必要铺垫与烘托。当然,我们绝不能因为空间纵深感的缺失便否认德莱叶和布列松的镜头中的“维度”,那是一种被德勒兹称为“动情-影像”(affection-image)的东西。不再赘述,然不妨细想一下,《扒手》(1959)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呢?


▲ 图1-2:《词语》剧照
而有些导演的作品,天然的带有让建筑师容易进入甚至沉迷的镜头,比如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比如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比如雅克·塔蒂(Jacques Tati)……再比如,本文着重论述的主角: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纵使他们各自之间仍有着千差万别,共同的、明显不同于德莱叶和布列松之处在于——物理空间某种程度上成为镜头捕捉和表达的一个重点。这无疑是会让建筑师们兴奋的点。
安东尼奥尼与“爱情三部曲”
在1950年代,当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的作品(如《某种爱的纪录》、《大路》)还可以算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之列的时候,他们便已经呈现出更多的诗意,“使意大利的电影拍摄从新现实主义的逼真性追求,转向一种含有想象与朦胧性的电影。”(见大卫·波德维尔《世界电影史》)自1960年代开始,二人都将拍摄对象聚焦在中产(及上层)阶级了。
安东尼奥尼在世界电影地位的奠定,始于1960年的《奇遇》(L’avventura)。这部影片,不仅对于安东尼奥尼个人,而且在意大利电影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奇遇》的忠实粉丝,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曾声情并茂的撰文《The Man Who Set Film Free》(发表于2007年的The New York Times):
“安东尼奥尼的视觉语言使我聚焦于这个世界的韵律:光亮与黑暗的韵律,建筑形式的韵律,以及被摆放在看似惊人之广阔的地景之中的人物形象的韵律。同时还有节奏,这节奏似乎与时间的韵律同步,移动的极其缓慢、无情,让我终于意识到人物角色的情感缺陷……”
斯科塞斯对于《奇遇》的盛赞,我是赞同的,尽管我无法像斯氏那般爱这部影片。我最心仪的是安东尼奥尼1961年的作品《夜》(La Notte)。《奇遇》、《夜》,与安氏1962年的作品《蚀》(L’eclisse),都在讨论都市中的男女情爱,后被合称为“爱情三部曲”。其中,《奇遇》和《夜》拍摄于米兰,《蚀》拍摄于罗马。
《奇遇》与《蚀》讲述的都是青年男女的情爱故事(尽管非常不同)。不知为何,这样的故事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比较钟情的是《夜》所讲述的一对中年夫妻的故事。故事上演的城市是米兰,发生在一天之内,时间和空间都相对紧凑而压缩。从影片一开始直至结束,我们看到的是一对在僵局中勉强维系关系的夫妻。丈夫是一位事业小成的作家,妻子出身中上层阶级的富裕家庭(职业未交代)。丈夫不停的被年轻美貌的女子吸引,妻子则冒险式的在城市中独自游荡。两人并没有放弃,仍然试图维持:妻子陪同丈夫去新书签售会,丈夫也主动袒露多情的行为,两人一起到酒吧看艳舞,也一起参与朋友的聚会,却在心神上各自漂移。这种僵化的、走向死亡的关系,从始至终的挣扎着。甚至在影片最后,夫妻两人在公园草地上谈心,希望贴近彼此,看似敞开了心扉,却也是徒劳无谓的、让人绝望的挽救。与《奇遇》和《蚀》一样,安东尼奥尼不交代结局,不交代未来,根本不去看(也看不到)未来,只是描述了一种状态。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中,我们看到迷茫的、飘忽不定的男人和充满疑惑的、甚至不知去向的女人,“离心式”的城市和过于浩瀚寂寥的地景。一种游荡的气质,恍惚与捉摸不定的气氛,飘散在黑白光影之中,也许,这就是影评人Andrew Sarris 所言的“安东尼奥尼式无聊”(Antoniennui)。
《夜》的人物及空间关系
《夜》这部影片,把我带入了米兰这座城,通过镜头感受它的白天与夜晚。一天之内,夫妻二人的活动区域是有限的,人物所处空间被限定在白天的医院、签售会、城市中、家中、酒吧,以及夜晚的朋友家、城市、清晨的公园这几个屈指可数的地点。虽然我曾在米兰短暂游览两三日,但安东尼奥尼的米兰与我看到的米兰是多么的不同:白日是热闹熙攘却漫无目的、迷离的人群,夜晚是有着雨水、轻风的郊外别墅,仿佛能够闻到雨水打湿泥土和草地的气息。
深焦镜头(deep focus)
德勒兹描述导演取镜有“饱和”和“稀释”两种倾向,他将安东尼奥尼的荒漠般地景归为“稀释”一类(应该是指《奇遇》、《红色沙漠》中的一些镜头),而《夜》的取镜,我想,是相对比较“满”的,很多时候趋向饱和状态——当然不排除“稀释”的取镜,比如朝向天空的镜头。但总的来说,大部分镜头往往比较热闹,城市中的建筑、景观元素多,人物多。安氏几乎不愿意把人物放在一个浅空间中,往往用深焦镜头,视觉空间重重叠叠。
安氏有多爱深焦呢?全景镜头能够展示开阔的场景和景深自不必说,在汽车这样局促的小空间内,因其前景与背景是运动中的城市,从而也带来视觉上的流动、延展感。当然,这也是长镜头的功劳。(图3-4)

▲ 图3:长镜头,车窗外的城市景观一直在变化

▲ 图4:车窗外的城市景深重重
拍摄浴室这样的地方,开间如此之窄,通过镜头方向、人物位置关系,刻意突出了空间进深,小空间也不显得逼仄。(图5)

▲ 图5:夫妻家中浴室
安氏酷爱将人物偏置,在场景调度中对背景做丰富化处理,安排动态元素,比如运动的车辆、人。在朋友家聚会的场景,几乎所有镜头中都有大量的背景人,他们在不同层次的空深度中跳跃、行走、谈笑,渲染了开阔而热闹的氛围(图6-7)。


▲ 图6-7:在朋友聚会上,通过电影镜头可见远处人物的运动
窗子和“镜子”
窗子和镜子,可以看作是拍摄深焦镜头的特殊元素。窗子是空间的延伸,镜子是影像的重叠。
先说窗子,这个窗是开敞、具有透视作用的窗,是一个opening。在此,做一个建筑师的类比,我们回头看看图1德莱叶的窗子,再看看图9-10中安东尼奥尼的窗子,像不像是Adolf Loos的窗对比Le Corbusier的窗呢?——插一段建筑学的故事。我们不妨想一下Loos的Villa Müller和Corbusier的Villa Savoye的开窗。显然不同于Corbusier的“建筑散步道”,Loos的住宅是具有“内向性”的,开窗不多,仅是为了采光,且窗户皆配有窗帘。Loos曾对Corbusier说,
“A cultivated man does not look out of the window; his window is a ground glass; it is there only to let the light in, not to let the gaze pass through .”
(一个有教养的人不需要看窗外;他的窗子是磨砂玻璃;只需要让光线射入,而无需视线穿透。)
Loos的描述与设计,多么像德莱叶在《词语》中对窗的处理啊!再回到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在丈夫的书房之中,房间本是一个浅空间,但打开的窗子(窗帘也被风吹的飘动)一下把室内扩展至了无垠的室外。

▲ 图8:Loos的Villa Müller东南角(摄影:刘泉泉)

▲ 图9:在医院,妻子在窗边眺望

▲ 图10:家中,丈夫的书房
再看镜子,影片中的“镜子”,其实是具有反射作用的、功效相当于镜子的玻璃。图11所示的城市一景,通过建筑一层临街面的大片玻璃,映射出了具有景深的城市容貌,多么曼妙!图12-15则展示了玻璃的透明与反射两重功效。镜子让我们看到了在一个固定视角看不到的另一面,比如图15中,朋友女儿的面容。

▲ 图11:玻璃映射出的城市景观

▲ 图12:妻子在城市中游走

▲ 图13:夜晚,朋友家中,丈夫看到朋友的女儿独自游戏

▲ 图14:夜晚,朋友家中

▲ 图15:夜晚,朋友家中。丈夫和朋友的女儿
(延伸思考:《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的镜子和人物位置关系。)
动态取镜与长镜头
安东尼奥尼不是文艺复兴式的视角,而是巴洛克式的流动和无限延伸。
有多少种表示空间延展的取镜方式呢?——其实,是以物理空间来表达对“画外”的暗示。安东尼奥尼给出了多个范例。如,汽车驶入镜,但是车身只露出一半儿(图16),建筑元素不完整,只拍一部分,且把“饱和度”高的建筑元素用较少的画幅表达,不均衡不稳定的画面带来动感(图17-18);再如,构图元素呈现倾斜状态,往往是由特殊视角的透视形成(图19-21)。

▲ 图16:汽车驶入镜

▲ 图17:丈夫回到公寓


▲ 图18-19:妻子在城市游荡

▲ 图20:两人在医院看望友人

▲ 图21:四人在医院病房
如果说,图17未拍完整的倾斜的入口大门是对外部空间延展的暗示,那么图18的构图更有意思了,大面积无任何装饰的光洁墙面占据了大比例的画幅,人物在左下角行走,俯视视角,加上画面两侧的高饱和度,影像有向外延展的意味。图20-21,拍摄医院病房里的场景,无论是夫妻二人,还是四人入镜,都使用了带有俯视角度的镜头。
这些都带来空间上的运动感,将影像拉向观众(如图16,前后方向),或者拉出镜头(左右、上下方向)。
关于长镜头,举一个也许比较极端的例子。相较图3白日驱车的长镜头,夜晚驱车时候如何拍摄呢?我很喜欢安东尼奥尼在此做的“小动作”。雨天的夜景,车窗外是迷蒙的城市,通过有节奏的光照的明与暗来表达汽车的运动,只有雨声没有人音,在明暗交替之中,隐约通过两人的表情和细微的动作来猜测对话的内容,所有的想象与诗意,通过时间的流逝缓缓淌出来。(图22-24)在此,空间的表达与景深无关了。在一个极其平面的影像中,观众依然感受到了汽车的运动,空间的延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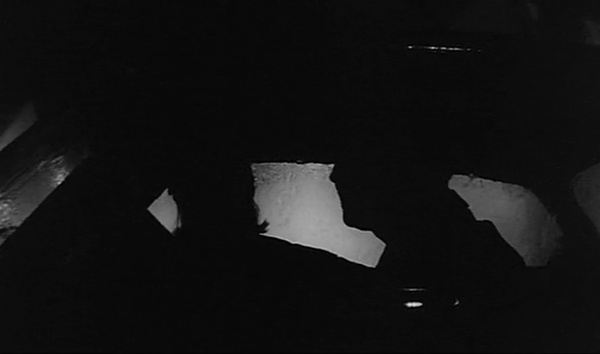

▲ 图22-24: 夜晚驱车,妻子与聚会上的男子
人物位置
在我看来,安氏非常喜欢在拍摄人物对话时,将所有对话者(甚至不参与对话,而只作为听众的人物)都包含在镜头之中,不是通常的“正反打”,而是这样的——近景是一颗硕大的后脑勺(图25)。在《蚀》里面,女主角蓬松的硕大的后脑频繁出现在镜头的最前最下方,这绝对跟审美无关,也丝毫不影响叙事,我把它看作安氏的个人取镜风格——“安东尼奥尼式脑袋”。这脑袋有着一种怪异的美学,也因为有了这颗近景的脑袋,人物关系、空间位置又多了一层。(图26)

▲ 图25:医院中,近景是生病的朋友的母亲的脑袋

▲ 图26:妻子在城市中游荡,下了出租车,与司机对话
再者,如上文已经讲述过(图21),以俯视的角度拍摄人物,将人物组织在一种人眼视点往往不可见的透视关系中。(图27)

▲ 图27:近景、中景和远景三层人物关系
再或,将人物置身于特殊的城市/建筑关系中。如图28,妻子离开签售会现场,摄像机完全可以摆在这道铁门之前(即不拍摄铁门),但是导演把镂空的铁门也取入镜中,空间关系又多了一层。

▲ 图28:妻子离开签售会现场
人物位置关系的设定,有时与叙事无关,有时与叙事相关。在夫妻双方参加签售会的这一场景中,两人第一次共同出现的镜头见图,两人一起进门,丈夫说了一句:“这是我妻子”,就头也不回的撇开妻子前去应酬。(图29)接下来图30的应酬场面,若不是细心的观众,可能都不会看到丈夫身后隔着几重人的妻子的身影。不同于前面几种情况,此时这精心安排的有些暧昧的人物位置关系,便与电影叙事相关了。

▲ 图29:“这是我妻子”

▲ 图30:丈夫忙于应酬,妻子淹没在人海
最后插一段安东尼奥尼利用城市住宅的空间关系来表达居住于公寓中的人的关系的镜头。(图31-32)同样的空间关系,在《蚀》里面亦有体现。这大概是建筑师们喜闻乐见的场景了。

▲ 图31:丈夫在公寓阳台,不经意望到另一座公寓

▲ 图32:另一座公寓的窗口
结语
上述刻意分门别类的几点论述,其实,在电影中都融合为一体了。我怀疑,《夜》这部影片的取镜和叙事都相对“饱和”,也许不能作为安氏风格的代表——其人物对白量远远超过了《奇遇》和《蚀》,紧凑的故事情节也使得它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多的“无聊”。
若我们对比一下《奇遇》,虽然同样拍摄于米兰这一座城市,但镜头中的城市却已大不相同。波德维尔认为安东尼奥尼的深焦镜头和长镜头有疏远观众的效果,让观众无从亲近、感受剧中人物。我倒认为,安氏的镜头疏远的不是观众,而是表达剧中人物与城市的疏离感。也许,《奇遇》更能够通过人物位置关系来诠释人物的内心情感,更能够表达安氏想要表达的无所适从。无论是在荒芜的小岛,还是开阔的城市,人物形象始终是迷失、动荡与不安的。
除了小岛上的荒辽,我很喜欢《奇遇》中的一个镜头,是剧末的一出,但不是那个被许多人(包括波德维尔)描述过的最后一幕,而是在此之前。男主角桑德罗追出门去寻找克劳迪娅,他发现了她,克劳迪娅在独自凭栏伤感。桑德罗看到了她,却没有走向她,而是径直的默默的走向另一个方向,走向一把(被安东尼奥尼摆设好的)椅子,坐在椅子上,陷入哭泣。(图33)

▲ 图33:《奇遇》剧末一幕
这可能是《奇遇》中最打动我的一幕了。
作者
刘泉泉,柏林工业大学建筑学博士在读,从事“电影-城市”话题研究;《Der Zug》建筑学独立杂志创办人之一及现任主编。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转载请通过邮件或电话与有方媒体中心取得授权。
上一篇:柯布行前讲座: 小人物让纳雷——关于柯布的8条观点
下一篇:董豫赣:石山一品|有方论园01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