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创始合伙人马岩松不拒绝媒体采访,但也不接受书面访谈。于是终于,在他的有方讲座开始前,我们当面以视频记录下了这“建筑师在做什么”第135期:马岩松,“好学生无法创造未来”。
文字见内容,视频见神态。
△ 专访视频PART A ©有方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MAD,有“疯狂”的意思,其实最早我喜欢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一种“文化搅局者”的身份,不像是一个传统的建筑公司。可是现在我们愈发觉得,我们的批判和反叛,最后更多是关于自己想建立什么东西。所以当我们能把自己实践的方向和发现放到全世界的不同区域中,我觉得特别让人激动,你在真正地实践当初的初心,通过建筑去做一个文化上的对话。
现在我们有机会去到美国、欧洲、日本,去不同的区域探讨这样的话题;当地的知识分子、建筑师、评论者都会开始关注你的思考,看你的作品跟当地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一旦做了一个东西,可能就成为这个地方的历史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属于他、成为他的文化了,这时对话才真正开始发生。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也是我们工作室里大家特别看重的一件事。所以项目不论大小,因为它能跟我们的思想产生碰撞、让我们思考自己在这个时代跟不同的文化怎么去对话,所以每一个项目都还是挺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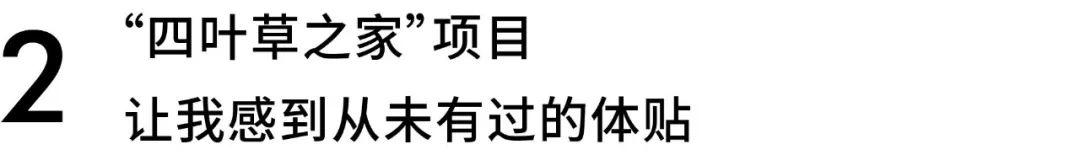
现在的建筑更多是一种产业,很多时候建筑师是在一个流程中工作,所以很遗憾,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跟历史和自己的生命有对话的角色。我觉得要把握住这个角色,你才有可能让自己困惑或是兴奋,让自己有种情感的反应。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这种反应,那将来不会有任何人可能跟你能谈到什么情感上的共鸣。
在中国的城市环境里,所有人都很自私,考虑自己这一块事;所以某个建筑往往是矛盾的集中体现,各方面利益、矛盾,都体现在这个项目里,它建成后就是一个怪胎,你能看到所有的顾虑都被不和谐地表达出来。在社会背景里,很多的建筑是产品、地产、政绩,有各种身份;可是对建筑师来说,你得把它纯粹地看成一个跟时间、历史、人对话的一种媒介。你投入了感情,将来围绕着它、使用它的人才可能投入感情。
这是我在日本“四叶草之家”项目中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这种情绪甚至会影响我做设计的态度,我清晰地感觉到一种我此前无法想象的对别人的体贴,突然变得很会为别人去考虑,为一个家庭,为一对父子,为某一个人五年、十年以后的生活去考虑设计。好像这才是建筑师应该有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已经久违了。这种体贴和情感的投入,无论你是做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还是做一个公共建筑、一个住宅,我现在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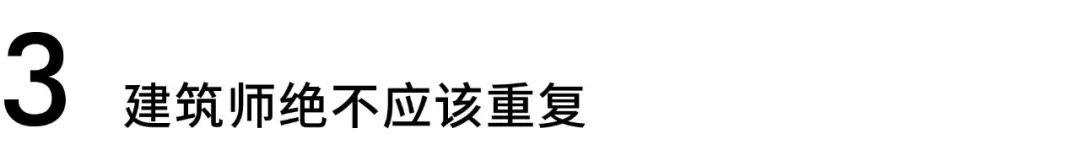
一个好建筑应该是城市中的一个催化剂,对建筑这个个体来说,它跟周边的差异化,它能在一个长时间不变的固有现实中去建议一种不同的未来,这是重要的。这个未来可能是针对你现在面对的问题,也可能就像曾有过的空想主义一样,不一定针对问题,就只是建议出一种不同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建筑应该做的,它不应该去重复。无论是已经有过的正确的东西,还是说错误的,错误就更不该重复了。
在中国,这种“拒绝重复”尤其重要。中国一直在重复西方那种现代主义的模式。它不但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而且很多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更何况在“这个”土地和“这个”文化环境里,如果你不停地重复“那个”历史的话,你就会丧失发现另一种未来和路线的可能性。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强的文化底蕴,如果一味重复西方,怎么从自身中发展出一种新的道路?我觉得首先要切断模仿的那条路,跟西方已经被认为正确的,或所谓“公认的”“权威的”这些东西划清界限,你才能逼着自己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在设计中我有我的挣扎,这个不用跟别人说。我接的每一个项目,都会考虑跟我的初心一不一样,我到底是谁。有时候有可能都不知道。所以你谈“坚持自己”的时候,可能更重要的问题是,你自己到底想干吗?在我提出“中国建筑师应该去考虑一个不同的未来”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每个人的答案都可能不一样,不用互相承认什么,或者有一种集体认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健康。中国做什么才是“对”的?我们大家都做什么才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对”的东西特别害人。
中国的建筑教育也备受这个影响,就是在学一种“经典”,学习历史中已被证明的东西,想成为一个好学生。但是好学生是不能创造未来的,也不能创造历史;你只能是在重复、学得非常好;但是中国现在的历史是要求你走出自己的路。三四十年这样迅猛持续的城市化,在历史中都很少见;但你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历程及建设之后,却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道路和思想,没有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建筑师群体应该对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全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环境,政治、文化都非常保守。建筑师需要挑战这个东西,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可能是唯一有机会的地方了。因为在西方,政治的气氛太强烈了;而中国因为建设的数量也大,文化上也还有多样性,中国建筑师应该把握住这个可能。
如果在50年的城市化以后,我们还在学习历史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那就非常遗憾。如果现在在中国的建筑、文化环境里形成一个多样的土壤,能兼容各种野路子,相信个人的作品、价值、他的思想和对未来的信念,那么这些个体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文化环境,要不然我们就只有一个“集体”。在集体中,人是没有价值的,他不会在历史中留下属于他的积极力量。


△ 专访视频PART B ©有方
有方 现在有多少个项目在同时推进?您跟团队的配合方式是怎样的?
马岩松 我现在工作的项目可能有十几个,有的在施工,有的在做前期设计,有的在深化。我基本是一个重复的流程,从早到晚跟每一个项目团队不停开会,基本要三天才能把所有项目过一遍。但是现在的项目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欧洲,所以就有很多时间在路上,于是现在许多时候就只能在微信上传图,或者用视频讨论等方式来工作。
有方 MAD在成立的前两年,差不多参加了一百个竞赛。在那些未建成的设计里,有哪个会让您觉得遗憾吗?
马岩松 没有,我觉得数量其实并不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你得有这个思考过程。那段时间我接触了很多真实的挑战,我现在所有的想法,跟那时候的会有一个思想上的延续。思想是一个慢慢成熟的过程,就像你上学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很多事,但是它的结果并不是为了能建起来,然而这个思考过程很重要。我现在甚至觉得那个疯狂做竞赛的时间有点短,就是让我再耗几年、再有三五年不中标,我觉得也没问题。你可能会考虑更多应该考虑的事。
有方 现在的MAD如何获得项目?
马岩松 有很多邀请,也有直接委托,但是一些重要的文化项目还是要通过竞赛。现在国际上一些挺重要的项目,好像老是这些家在参与角逐。我发现好像一方面世界变得很保守,很多的城市建设都搞得非常商业,不想去实验、没有勇气去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你还能看到一些非常有独立价值的设计师,保持着对一些重要竞赛的参与,大家还是能经常碰到。我觉得这是我做竞赛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从来不强求说哪个项目应该是我做、我一定要赢哪个,从来没有。无论是做真实的项目还是竞赛,只要它能让你有一种对话,能刺激到你自己的价值、和他人产生一种价值观层面的碰撞,我就觉得值得。

有方 对您作品的评价中常见“感性”“浪漫”“灵光一闪”等词语,它们是您个人设计风格中一以贯之的突出元素吗?
马岩松 如果你把建筑看作是一种与文化、艺术相关的生活体验,那可能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创造它的时候,能有灵光一闪的瞬间。就像我们喜欢的那些过去的建筑师,他总是有能打动你的地方和共鸣,作品跟当时创造它的人在情感上的投入有关系。这种情感投入,肯定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在设计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然后这个方式就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回味至今。这个状态当然是我最想要的,但并不是在每个项目里都能有这个状态。
有方 作为“首位在海外赢得重要标志性建筑的中国建筑师”,对这种国籍、身份认同的谈论,您觉得在什么程度上是有必要的?它是一个值得被强调的标签吗?
马岩松 其实说实话,在海外你参加很多活动或者去做建筑,没有人很敏感于你是唯一或者少数的“中国建筑师”。他们觉得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同时城镇化进程和建设这样迅猛,怎么可能没有一定数量的建筑师去到海外来做建筑?这点其实国外没有那么关注,但在中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确实是在谈这件事。
我不太介意中国谈这件事,我觉得中国也需要这种讨论,应该考虑自己的文化身份,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危机。很多人自身有文化危机的时候就想,我是应该搞传统的、古典的,还是做现代的,还是应该结合?这类反思从梁思成做大屋顶的时候就开始了,到今日也一直在探讨。这个危机感我觉得会保持,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一直有危机,但是找不到答案。对我来说,我也好奇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从哪来的。我们这代人去美国上学,又在外面有过实践,好多人老问我“扎哈对你有什么影响”“在美国求学对你有什么影响”;可是我会觉得,好像我的童年、我在北京这城市里的长大,这个传统的环境对我的影响更大。这个城市其实是一种传统价值的凝固,把那些无形的思想、哲学都凝固在环境里,然后又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一种影响,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人,他自然地会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观;而只有到了西方,你才会发现自己的不同。其实你要相信这个不同,不是因为他们先进而我们落后,而是因为正是此不同才可能把你带到一种不一样的未来,而且这个未来还可能对西方产生影响。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们应该固守传统,或者刻意与西方相区别;我觉得是应该往前走一步。




有方 您此前一次采访的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您说“我喜欢的那些伟大的建筑师都是博爱的人,他们对这个世界很有爱,但这也造成他们其实是悲剧人物,因为有太多美好的东西实现不了”。这些“悲剧人物”是谁?为何会有了这种感受?
马岩松 我说这段话的时候,应该是前几年我们做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但是在芝加哥引起了很多争论。后来弗兰克·盖里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支持我们的方案。他说我们很年轻,应该给我们机会,看最终会做成什么。后来我就去拜访他,成了朋友,他就是一个我说的这种特别可爱的人——盖里一心想要在这样那样的项目中,把自己那些奇思妙想给你,但是他一辈子面对的都是拒绝。别人一直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各种各样的碰壁。但他就是始终充满热情,不了解别人的残酷也听不懂别人的拒绝,一定要不停地去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想象……但是最终,建筑师不是一个决策的角色,所以很多项目还是实现不了,还是有很多遗憾。

另外历史中比如像高迪,当时喜欢他的业主和人也不多吧;还有像密斯、扎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受到太多争议。但他们就是把表达自己和让自己跟历史对话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 一直想表达然后一直被拒绝,我觉得这可能是建筑师的一个宿命吧。
如果你看重眼前的成功和“被接受”,因为追求“和谐”的关系和对现实文化的融入而放弃了长远的愿景、你对历史的真实的反映,那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后者才是历史给你的责任。现世的所有争论都是临时的,每个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认知;但是百年以后呢?只有建筑还在那里。我们为什么今天还去看那些所谓的经典,它们功能已经不一样或者不在了,但却还是能给我们感动?是因为人类还是有才华的,我们的文明记载在这些建筑中,这些建筑来自建筑师当时的热情,他们不在乎被拒绝。所以我觉得,可能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个悲剧人物,你才不会慌张,不会觉得好像这个时代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不接受我。我觉得这才是正常。

日前,MAD蓬皮杜永久收藏个展“MAD X”已开幕,欢迎前往一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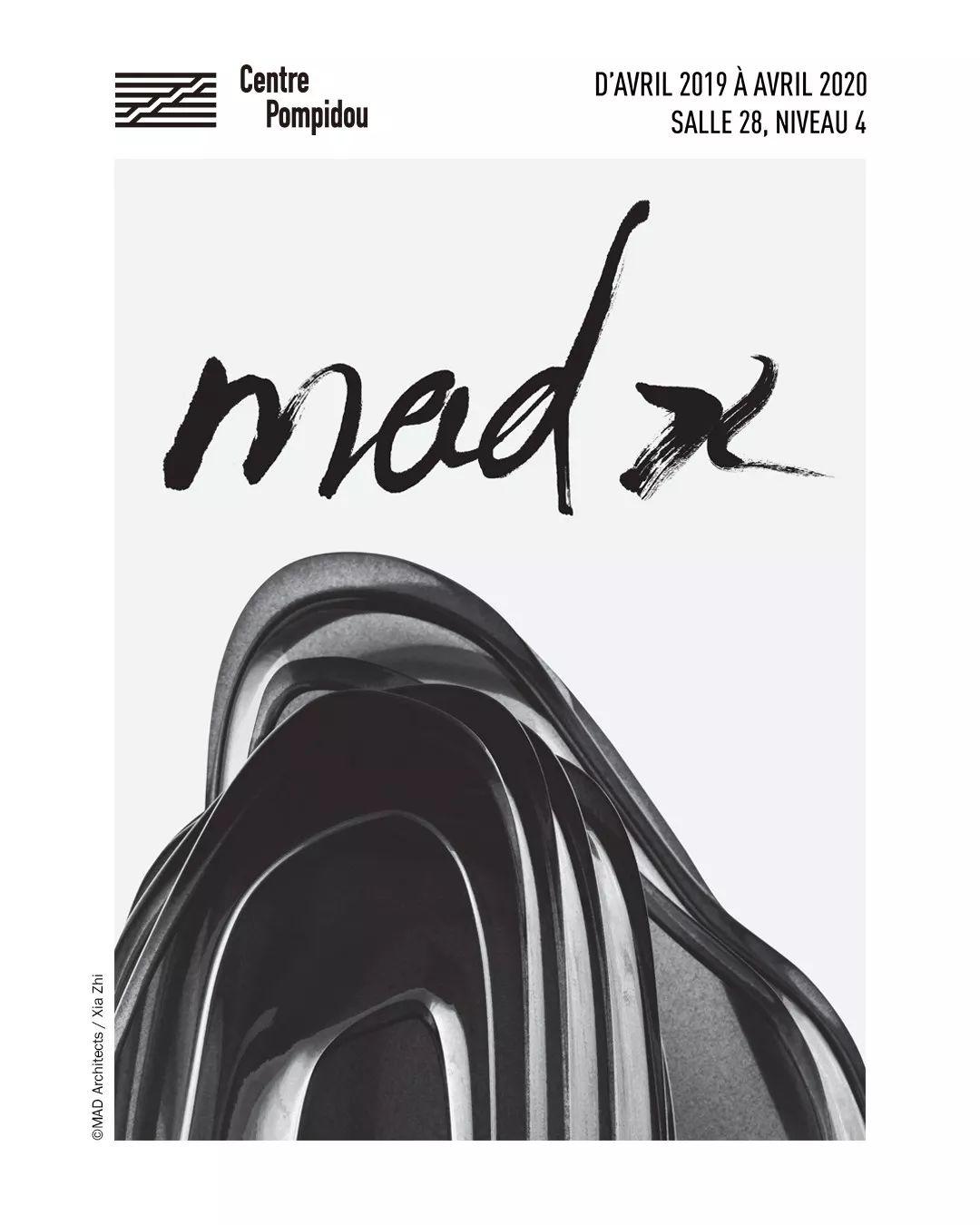
采访 / 原源 摄像及剪辑 / 阮凯、郭嘉
视觉 / 李茜雅 校对 / 鲍思琪
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欢迎转发,禁止以有方编辑版本转载。
上一篇:重塑人文品质:三河村村民活动中心 / 垣建筑设计工作室
下一篇:经典再读23 | 柏林爱乐音乐厅:德国建筑的战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