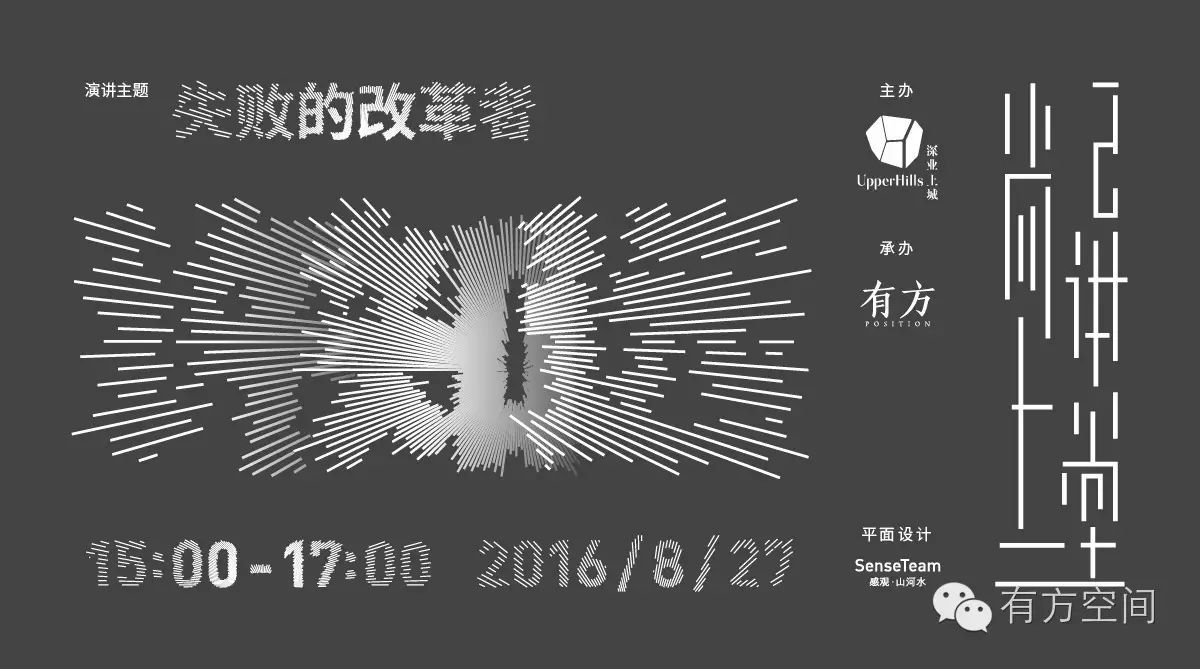
编者按:8月27日下午15:00-17:00,深业置地主办、有方承办的尚上讲堂·第2季 | 许知远——“失败的改革者”讲座,在深业上城举行。以下为讲座全文:

演讲 | 许知远
边陲之地容易被忽略,但也可能因此带来意外的生机和自由
我对深圳有另一番的情感。深圳处于边陲之地,它有可能被忽略、被遗忘,但也可能因此而带有意外的生机和自由。中国整个历史的主题,都是在边陲和中央之间的纠缠,边陲的兴起和中央的衰落,或中央再次兴起和边陲的衰落,不断地往复交错。三十多年前,这里只是一个渔村,短短的时间内兴起这么多的高楼大厦。身边有一些香港朋友谈到,他们表示非常忧虑,是不是十年之后香港变成深圳的另个一个区。这样的一种新的情绪,是这个时代主要的情绪,背后代表的,是中国重新崛起带来的巨大影响。
三十多年前,当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是一个让人神往和惊心动魄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代表着一个崭新的世界。经过多年的封闭之后,我们对世界所知甚少,我们对自己所知也甚少,我们过去是一无所知的。
当年,包括袁庚先生在内的那批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者们,他们被迫进行改革而非主动为之,因为他们看到大规模的逃港现象无法压制,人们穿过深圳河的边界时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同样是中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直到今天,当我们叫喊“深圳崛起”的时候,如果坐火车穿过罗湖关口,看到的仍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香港代表某种更复杂、更细微的元素。在此刻,许多人丧失了探讨的欲望,完全被一个更空洞的概念、更宏大的规模所吸引,而忘记了内在的区别。

十九世纪的中国身处风雨飘摇中,但同时新一代人开始崛起
在19世纪中后叶时,,中国也曾经有过一次巨大的中兴叫“同治中兴”,以同治皇帝命名的一个历史阶段。当时,中国面临内交外困的处境,一方面,从外界来讲,英国人、法国人来到中国的沿海,从1839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860年火烧圆明园,在这二十年时间里,中国看到了一个陌生的挑战者从一个陌生的世界到来。但这样的外界的挑战,仍然是边缘性的,他们出现在广州,出现在上海,出现在宁波,出现在舟山群岛,出现在天津,当然也暂时性地进去了北京。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面临的一个更大的挑战,是内部的混乱。从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起义,巨大的农民战争的混乱,席卷了整个南中国,造成了将近5000万人的死亡。
咸丰皇帝在1861年逃到热河时死在了那里,中国身处风雨飘摇之中,但同时新一代人崛起了。一方面,因为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恭亲王奕䜣暂时被任命管理看起来已经失效的中央政权。他与西方人打交道时,非常意外地发现,他们竟然也讲道理,并非蛮夷。另一方面,在地方则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崛起。他们从自己的省份、自己的家乡招募军队来抵抗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真正让他们焦虑的,不是推翻清王朝,而是因为太平天国信仰一种被扭曲的基督教。他们认为这是对儒家社会秩序的巨大的逆反,所以他们要奋力保护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

从1860年之后,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中国达成了一种新的奇异的平衡——政权被摧毁,大量人口被消耗,而消耗人口意味着新的空间涌现出来,因为之前的18世纪中国人口从一亿多增长到了四亿,人口的压力意味着生存压力,导致各种新的问题。大平天国消耗了大量的人口,土地重新被开垦。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一个新的政策,某种意义上,像是改革开放。当时,中央在北京建立了总理衙门。在此之前,中国对世界实行的是朝贡系统,通过理藩院这一部门对外联系。外国人两三年来朝贡一次,主要是做贸易,朝鲜人会带着高丽参,缅甸人、越南人也会带着自己的特产过来北京交易,某种意义上就是现在的“广交会”。当时中国的世界是有着鲜明的等级,外面是外夷的世界,接着是藩属的世界,再是更远的世界,这是中国人的世界图景。
1861年时,突然成立了外交部前身的总理衙门。在中央,创办了同文馆,学习其他语言,培养外交人才,理解西方的理念。在地方,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他们创办了新的轮船公司,新的兵工厂,培养人才,这些新的力量开始零星地出现了。
在这同时,欧美世界也转入自己的混乱当中。美国人忙于消化自己南北战争的后遗症,欧洲在争夺非洲的同时,内部出现新的混乱,他们没有心思把精力放在亚洲。当时的国际系统是一个相对和平的系统,而同时中国内部正在进行一次伟大的更新。从1860年初开始,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到1880年中叶的时候,中国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整个世界对中国有了一种新的惊叹。

这些改革者们,他们没有太多可以失去,所以会拥抱一种新的东西
尤其到1887年成立的北洋水师,创建了亚洲排名第一的舰队。当时的欧洲媒体,充满了有关中国已经醒来的论断,充满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可能成为新威胁的看法。而且最恐惧的一点是,他们认为,如果自强的中国和明治维新的日本相结合的话,那就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亚洲力量的兴起,将对欧洲的秩序造成巨大的挑战。这是当时在西方媒体上非常重要的论调,而中国人自己也参与了这样的说法,最主要的倡导者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作为当时见过世面的外交官,他曾经被派驻英法作为大使,直到1880年代末才回到北京。
在1887年卸任之前,曾纪泽发表了一篇英文的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世界上许多媒体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的《申报》也转载了它。文章中一个核心的论调是:中国曾经沉睡过去,但是到了火烧圆明园时代,发现自己的眉毛、头发被烧着了,它被惊醒了,它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此文在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也激起了一些不算重要、但很锐利的反驳声音。
何启就是其中一位反驳的发声者,他是香港的最早一批华人立法会议员,也是香港华人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写了一篇文章反驳道:中国的变化只是表面的,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政权和人们的关系到底是密切还是紧张?人才是不是得到充分尊重?教育有没有重组?有没有尊重基本的商业条款?有没有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又怎么能够说中国已经醒来了呢?
何启的论断,是个边缘性的声音,他的判断跟反驳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人听到并关注。七年之后,人们就发现了新的结果。1894年中日在朝鲜发生战争的时候,国人遭受到当时中国在亚洲崛起这一论断的巨大打击。一直到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之前,所有的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必将获胜,但结果是颠覆性的,在同治中兴的表面辉煌之下是千疮百孔。1898年的政变失败之前,国人开始了新一轮对改革的巨大讨论。
在1894年的时候,一些人突然意识到何启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19世纪中后叶,在上海,在香港,包括在广州,涌现出了一批人物,其中最早出现、最重要的是王韬—— 一个不太成功的科举应试者。出生于1828年的王韬,因为父亲的关系,1840年代末来到上海为传教士工作。当时包括王韬在内的读书人,相信所有人生道理跟所有治国的方略都在四书五经当中,只要学会像孔子、孟子一样思考,就能应对复杂的世界。但是他却要为一个传教士工作,内心感到非常屈辱。但同时也是在上海,他第一次喝到了葡萄酒,见识了印刷机的高效,目睹了让人震撼的外滩新古典式建筑。他觉得这是不一样的世界,蕴含了许多新的东西。在上海的那几年,王韬既面对新世界,同时又发现自己陷入无法从旧世界摆脱的痛苦之中。
王韬跟当时的两位好朋友,他们三个人没事时就在上海的城隍庙一带,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他们称自己是“海天三友”,天天酗酒。他们内心的痛苦是,虽然自己看到了一个新世界,却无法把这个新的世界以及对新世界理解的方法告诉自己的同胞。他们无法把新的知识转化成某种现实的力量。所以,在1861年时王韬一度想投奔太平天国,但也因此成了清朝的通缉犯,从上海逃到了香港,在香港客居了很多年。他帮助一个英国人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后来去了英格兰住了一段时间,写了关于英国的游记,然后回到香港办报纸,发表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变革的看法。因为李鸿章的关系,在1880年代,王韬回到上海,成为当时格致书院的院长,直到1897年死去。
马相伯,上海人,复旦大学的创始人。他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精通法语,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待过。他活到1930年代,但他同样终生无法将自己的理念转为现实。
黄遵宪,梅州人,爱国诗人。他在1880年代末写了关于日本的最早的著作,探讨了维新对于日本的影响。但这本书直到十几年后才得以出版,大大的延缓了中国人对日本的理解。
容闳,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耶鲁。他回国之后曾经进入过曾国藩的幕府,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创举——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学童,里面涌现了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修建了中国最早铁路的詹天佑。

上述的这一群改革者,他们看到了外部世界是怎样的,但是却无法进入权力的核心,他们最重要的需求是成为权力核心中人的助手、幕僚,他们是当时的中国官僚系统里最开明的一批人。但这批人又每日生活在战战兢兢和谨慎之中,他们没有力量把理念更好地付诸实践。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我们最初是看到战争的失败,我们比不上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一旦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仅是坚船利炮,而是整个制度出现了问题。所以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的中国,议院制度是一个被探讨得非常多次的概念。再往后些,中国人意识到,有可能是更深的文化层面出现了问题,于是出现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
关于制度这一点,其实是严复发出了最开始的声音。严复在1898年出版了他的《天演论》。这本书的许多概念后来成为了流行语,影响了很多人,包括鲁迅、胡适之、毛泽东等等。而里面最重要的核心是,严复第一次地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意识到,西方富强世界的思想里面与国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具有某种更高的优越性。
严复的这样一种声音,在当时经历了非常迟缓地被接受的过程。这些改革的失败者们,最初进入洋务的这一群人,就像三十多年前开始闯深圳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单位或地区都属于边缘者,他们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所以他们会拥抱一种新的东西。
年轻时严复被派到英国读书,再回到福建,后来去了天津,担任水师学堂的总教席一职。他一生都觉得不得志,直到翻译出了《天演论》,才因此缓解先前的焦虑。但是,即使对李鸿章来说,如果一个人不熟悉儒家经典,没有在科举制度上获得功名,那么他所有的陌生的知识都是不被尊敬的。知识的力量在这个国家是多么脆弱,它们很容易被压制于现实权力和权力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每当中国发生了某种更新,有了某种生气勃勃的时刻,一定是由沿海的冲击带来的,一定是由于某种意义的中央政权的衰落带来的。它给予了这个社会某种新的自由。在这种新的条件下,边缘的力量开始迸发出来。

我特别希望看到伟大的时代会再度到来
19世纪末所有的变化,从同治中兴开始,我们看到的是沿海力量的兴起。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经济政策、人与制度的关系,他们都有一套非常丰富的论述。但是阅读这些论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悲哀,因为很容易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我们并没有一种新的创造,或者更复杂的创造。因为我们面对的始终是那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出于恐惧的原因也好,出于各种其他的原因也好,人们无法把自己的思想进行更大的拓展。而此刻人们又似乎感觉到处在一种新的历史循环中,在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巨大的混乱和自我摧毁的动荡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社会重新开始变得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看到了陌生的世界、新的世界。
经过三十多年,当我们感慨过去王韬的知识、何启的知识、严复的知识,这些关于西方的知识没有进入到现代社会或者被极大地延缓的时候,现在我们又开始感觉到此刻自己对世界的知识又开始被封闭起来了。就最狭隘的来讲,我们似乎又开始错过了硅谷在过去十年发生的巨大技术浪潮,因为我们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局域网里面,沉溺于自己创造的某种大公司的狂欢,却已经错过了这十年产生的非常大的变化。
重温这些历史,对我来说,可以因此找到一些新的安慰,新的动力。
在刚刚提到的那群19世纪的改革者身上,仍然有些是过去中国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先的东西,他们身上那种力量,有点半宗教式的力量,是社会特别重要的动力。只是我们这个时代太不相信崇高了,太不相信伟大了,太不相信超越自身利益的力量了,所以变成了这么一个有点萎靡的小时代了。而当时的他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不同的方向,一个伟大的社会或时代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中,有的成为政治人物,有的成为学者,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成为建筑师,我特别希望看到这个时代会再度到来。

提问: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国家对自己思想的研究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逐渐出现的。当中国近代的改革者们面对西方的这一套思想变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一个直接现成的东西可以接触。另外,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看, 尤其是20世纪西方对他们本身的思想史,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思想发展的研究,最终的变化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并不是完全由自身的思想变化发生的,至少变化之初受到包括来自当时的北非、东方的中国等各方面的影响,然后才逐渐发生和变化出来的。
许知远:当我们面对新的文化冲击时,某种意义上有种像膝跳反应——突然有一个东西打过来,腿会本能地弹起来,文化也是同样的道理。面对陌生的新事物的时候,我们首先会从自身系统寻找某种参照物去理解它。19世纪中后叶时,中国有了驻外公使,以及出外旅行者、留学生等人。
当时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他对19世纪中后叶的伦敦、巴黎是这样描述的:伦敦、巴黎的生活,就像国人想象中的尧舜禹时代一样。在之前,中国人对外部的理解,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落后的,而在19世纪末,终于意识到有比自己更强大、更文明的社会。对当时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们,在当时完成了许多西方的翻译。翻译中传送的理念是,文明强大的西方世界并不陌生,它只是实现了中国的“三代之治”,只是实现了中国人的治国理想——这些东西我们古已有之,只是暂时忘掉了,而在西方世界里实现了。
提问:西方是怎么样在宗教改革之后发展出来一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变革者知识分子在试图努力传播西方的东西,但他们是否真的很清楚地知道西方是什么样的呢?
许知远:这些变革者知识分子们要用自己的语言来消化这个东西,这也是严复为什么在历史过程中会显得那么重要。因为一个新的东西需要新的名词来描述,旧的名词不能描述新的东西,所以严复这些人要创造新的名词。那时候“科学”、“技术”、“民主”、“宪政”都是崭新的词,他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来理解新的变化。
西方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概念,中国也是如此。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是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写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书中提到,通过严复的观察,作者本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西方。西方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各种冲突、各种问题、各种复杂,他们对自身也难以解释,而严复发现了中国看待西方的方式—— 一切都需要寻找力量。
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纯粹是依靠文化或某种精神上的东西(推动的)。中国19世纪末之后遇到的很多挫败,很大程度是因为政治的封闭和政治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而欧洲从来没有面对过单一的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状况。一个社会的变化和动力,都是由于多元的价值间的碰撞所带来的。19世纪这群改革者们面对的无奈,是一种官僚和政治系统,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瓦解这个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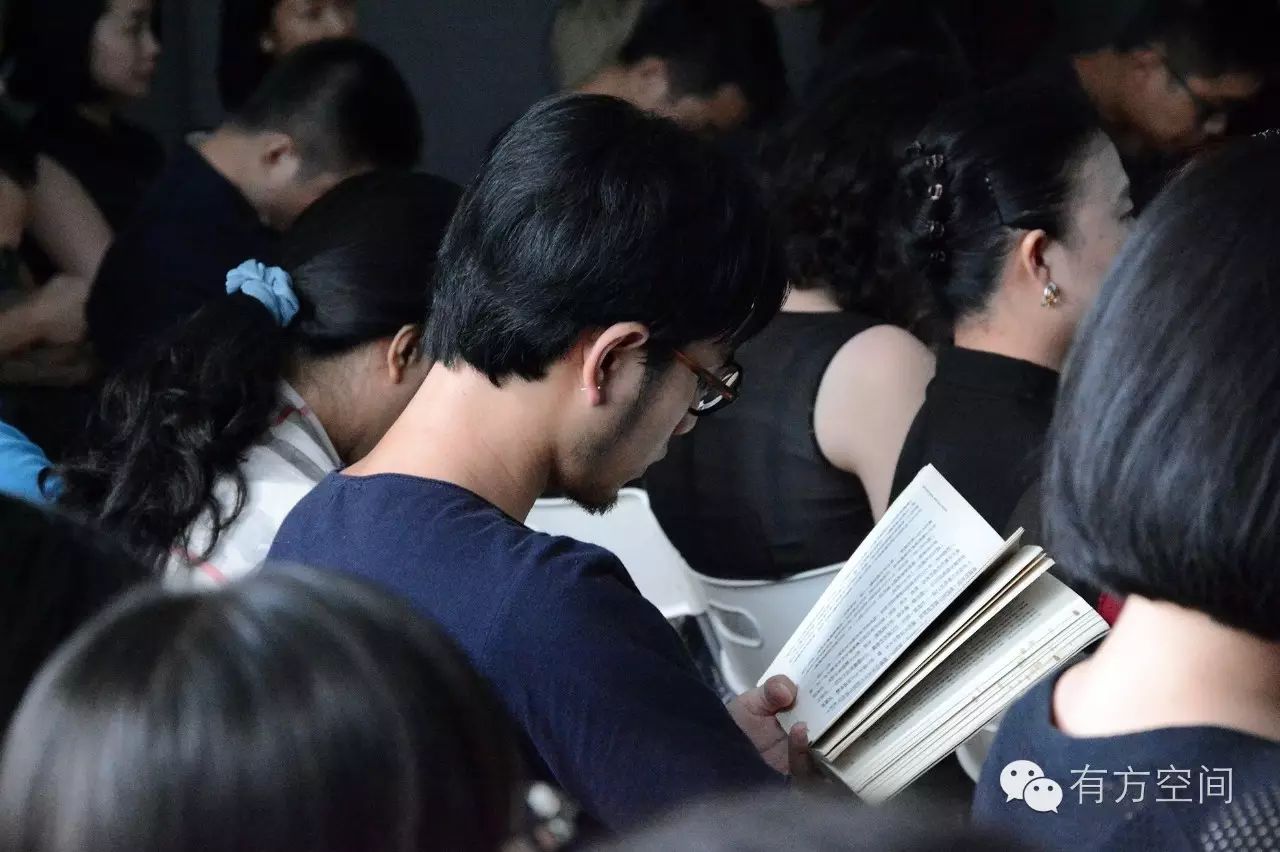
提问:在当下,知识分子该怎么生存?是否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知识分子了?
许知远: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新技术革命。任何一个新技术革命刚开始都是起到了瓦解的作用,使得旧的价值观被瓦解,新的价值观不断地形成。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庸俗的大众标准获得胜利,而知识分子的标准遭受瓦解、被攻击。但这是一个过程,他们会重新创造新的秩序、新的变化。思想的生命力是靠长度来应对现实的力度的,它在此刻可能被压制,被暂时性遗忘,但是它们会被重新唤起。比如王韬的改革建议,在20世纪初的时候被许多国人认可,影响了很多人。
思想本身具有的生命力,会战胜很多东西。此刻的中国,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够强大。我们的知识水平生产到底怎么样?我们的写作,我们的思考真的能够领先于整个时代吗?我们真的能够创造出一种自己认为重要的叙事方式、思维方式,帮助其他人感知到现实困境吗?
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狭义地当作一个发牢骚的人,那他当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缺乏内在价值的群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创造一些更内在的、更有力量的东西。在恰达耶夫悲叹俄国面临多么糟糕的状况的同时,十多年之后俄国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够直接应对政治的压力,他们把所有的感受、力量变成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们不仅影响了俄国,而且还影响了欧洲、影响了世界。
我觉得归根结底都是创造力本身。如果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创造力不够的话,那所有的脆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活该。在一个感觉到压抑、破败、瓦解的时代,找到自己内在的东西很重要。比如现在占主流的腾讯也好,阿里巴巴也好,在二十年前也是边缘的、破败的、瓦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说法。

提问: 你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你有过绝望的时候吗?因为我们知道鲁迅是绝望的,他只是为了给别人带来希望,在坟上插了一朵花。
许知远:我没那么多使命感。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我没有那么多绝望。当然,在过去一个世纪,知识分子处于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比如说在1898年,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当时的下层官僚仍然可以在权力中心里尝试去做一些事情。而到了五四运动时,胡适之、鲁迅他们仍然可以对这个时代有很多影响。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变得部落化了。在过去,我们依附在士农工商的精英结构里面,但现在被打破了。知识分子没有所谓的精英结构可以依附了,所以变得边缘化,但这个过程恰是一个寻找自身的过程,可以重新去捍卫知识的权力。
另外,其实我没有那么多使命感。我也不觉得鲁迅有那么多大家想象的使命感,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下发生的。但是我相信知识分子要有某些超越的东西,超越于自身的利益,自身的价值、考量和追求,要有对更美好的世界的寻求。我们的很多沮丧并不仅仅是眼前的失败。不管是制度也好,生活也好,都有另一种可能性,需要我们去寻找另一种可能性的过程。而现在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美好想象在消失,在退化,我们大家都认为只有此刻的生活,这个是让我们非常不舒服的。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想象能力,乌托邦能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提问:在民族性方面有没有什么看法?
许知远:我不相信“民族性”这个词,它是一个复杂因素的混合体。台湾是另一个社会,海外华人社区是另一个感觉。制度对人的塑造是非常大的,时机对人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不相信一个本质问题能解决很多东西。此刻的日本跟1940年代的日本肯定不一样,跟明治维新时代也不一样,跟德川时代也不一样。历史变化是由很多不同因素在猛然之间完成了某种混合或化学反应产生的。我不相信有某种清晰的解释,如果有某种清晰的解释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研究孔子,就可以支持自己做的所有事情了。

提问:这个题目叫“失败的改革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870年代之后太平天国覆灭,到1895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GDP几乎维持了10%以上的增长,这在世界的经济史上可以称得上是奇迹。在甲午海战之前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人甚至世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甲午海战爆发了,中国失败了。甲午海战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直接的创伤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更为致命的后果,有没有可能是当时中国所谓的精英分子,所谓的优秀想要改革的人,他们开始怀疑中国过去这二十多年所走的路,他们希望可以颠覆性的、甚至是一蹴而就地实现某一种改革。而这样一种很激进的想法,我认为像梁启超、康有为,他们根本没有想清楚他们要做什么就行动了。有没有可能是后面这一群想要把国家很快变得很好的人破坏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你认为甲午海战这样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中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吗?假设没有甲午海战,中国的进程在当时既有的政治框架下,如果由当时的改革者继续良性推动,它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许知远:首先,我很难大胆去假设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当时的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悲观,就那段开放时间不是在1894年结束的,在此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比如曾纪泽1887年回到中国后,他在总理衙门任职,当时给中国外交界带来一股新的风气,因为他会去别的使馆,也会请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来家里喝茶,他的女儿会讲英文,可以跟外国人交流。但很快他的行为作风引起了各种非议,使得后来曾纪泽越来越少参与外交使馆的活动了。而紧接着,中国新的一批外交官成长起来了,他们在同文馆受过教育学了英文,早期还出过国,但是这批人比上一代人更保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出身不正,是学外语的,不是从孔孟之道的儒家系统中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的出身不正,需要通过加倍地对西方表示强硬来确定自己的合法性。
不管有没有甲午战争,中国既有的权力封闭性,一旦重新获得权力和财富,就会压跨所有的创新。1895年在北京的官员的谈话,他们的日记,充满着无知、自以为是的傲慢。在当时,新的封闭状态已经出现了。即使在甲午战争之后,改革者要实行改革,仍然非常困难。生活在那个时代,很难说梁启超、康有为是激进的,有时候我们对当时所谓的朝廷有很多一厢情愿的期待。
提问:我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参照物”,你一开始讲看到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对比。当我去看台湾的时候,了解台湾的很多事情。台湾人跟大陆人很大的差别。我个人角度觉得,我们并没有一个参照物。我们今天讨论知识分子或者社会人能做什么的时候,反观台湾做的事情,我觉得他们能够基于自己身边的很多事情,反而觉得从个人的点出发,去做一些事情去影响别人,这才是当下社会变得更好的方式,而不是从一个非常大的点切入。对于参照物这一问题,是否有一些参考的看法或分享一下观点?
许知远:我有点质疑这种论调。很多人会说,在成熟社会里关心的是“小确幸”的生活,而不是整天关心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否想过,1970年代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的?1980年代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没有经历过巨大的、纠缠的社会转型的斗争,我们怎么能去接受那个呢?我们怎么能够确保“小确幸”的生活呢?他们是经历过这个变革的,比如林生祥能够“一言不和”就去保护美浓水库,是因为他们经历过1970年代台湾的抗争,他们有这个权利。但纯粹的台湾“小确幸”,也是很无聊的生活,如果没有对一个新的历史的可能性的向往,那么生活也就缺少意义。人总是有一个对更高秩序的渴望,这个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它是通过跟他人,或更广阔的历史结合才能实现的。纯粹的个人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无聊的生活,人都渴望更大的一种力量和生活。
我觉得在某些不同的切面是有不同的参照系的。寻找这些切片并不是说这些参照系能给我们某种指导方法,而是我们在类似的经验当中寻找到了共鸣,是否能给我们启发。人都是在与他人的确认中找到自我的,这个参照系始终要存在,以此来不断地确认自己是谁,自我分析。我们不能认为一切的生活都是想当然的,只有在碰撞当中,才能确认自己生活的边界、问题、困境、可能性,以及美好之处。
编辑 | 林楚杰
摄影 | 李菁琳 林楚杰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归有方所有,如需转载,请后台与有方新媒体中心取得联系。
投稿邮箱
media@archiposition.com
上一篇:尚上讲堂第二期 第三场|胡如珊:怀想·反思·城市|有方讲座
下一篇:上海虹桥的未来文艺地标——虹桥天地演艺与展览中心,如恩设计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