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员王珞丹来到建筑圈,以12期《丹行道》,与12位中国一线建筑师聊了聊天。
一边在银幕上演绎别人的喜怒哀乐,一边却隐身于建筑背后探索自己的空间表达,如果建筑和人都是容器,他们要感受什么?吸纳什么?又将留下些什么?
《丹行道》第5站,五维茶社里,从王珞丹喜欢玩的乐高谈起。
视频已于10月31日在新浪微博播出,更多精彩于此呈现。

王珞丹 您建房子我会觉得很像在搭乐高。
袁烽 可以说是很像乐高。乐高是预置单元化拼接的一个最典型例子,只不过乐高的单元比较小,如果用大的乐高搭一个客厅那么大的空间,那就是不得了的工程。伦敦大学有一个年轻人叫Gilles Retsin,大概是1984、1985年的吧,已经做到研究生课的负责人了。他明年夏天会来同济,他做的事就是像搭乐高一样搭木结构的房子。他的每个木结构构件都比我们沙发还长,每根上面都有接点,像中国的榫卯结构一样。可能一整个的房子都是这样的构件搭出来的,很有感觉。搭建的原理也跟乐高差不多,只不过尺度不一样—— 一个乐高的构件可能只有十公分,五公分;他一个木结构构件可以到五米,十米。
王珞丹 更大了。
袁烽 我们在建造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更大的,机器人的所有建造和打印都不是小尺度的。现在几千块就可以买个台式的3D打印机,打印小物件。而建筑的空间和构件比较大,虽然背后的原理可能很接近,但是面对的尺度不一样。尺度大了之后就要切分,本来可以整体打印一个物件——比如一个杯子——在尺度变大以后就需要把它切成单元,否则没有办法运输。如果我们要通过卡车把构件运到现场,那么卡车的尺寸有时候就变成我们生产的规定尺寸。
像我们今年在威尼斯双年展的搭建,用了大概四个最大的海运的集装箱,对于“所有构件能否放进这四个集装箱”的考虑,就影响了打印的规格。到了现场,切的越碎的单元拼起来就越容易倒掉,我们叫“离散化”;离散化越小的单元拼出来越不结实、越大的拼出来越结实,就是这个原理,这背后都是一个计算。


王珞丹 我很喜欢玩乐高,玩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已经开始买一些散装的零件,做永动机什么的。我从世界各地买各种零件回来然后搭上,看怎么让它运转;有时候你会发现哪个地方搭错了一个小的零件,于是永动机就不会动了。然后我去开始研究他们的模具,是如何做到零误差、让每个零件严丝合缝地叠加在一起——我此前总觉得那么多不一样的零件,总会有误差,后来发现完全没有。
袁烽 搭乐高在流程和原理上,跟我们现在做的数字化建造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想在短时间内有效率有质量地建成一个房子,就需要非常严密的控制。一个房子虽然看上去简单,但是它背后有太多你不能够预测的东西。比如我们在西岸做的那个网壳,看上去仿佛每根木梁都很细、很轻,但为了实现这个结构,每根木梁都有细微的、肉眼很难辨认的差异。如果搭错了乐高,你还可以拿下来再重新装一下;而对于尺度大的建筑,这么大的构件用吊车吊上去了,如果装到第11个你才发现搭错了,又要重新再装前面10个,这就肯定没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数字化设计建造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挑战。我们沉浸在里面的原因就是,有时候整个过程有点像侦探小说,大家一起来破案。你在做设计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模拟一遍,而最高水平的模拟是非常准的,出错率是0。如果你觉得三下两下就能模拟好,那么在实践当中就会发现,你其实只预测到3个难点,但是现实当中有30个难点,那东西肯定是建不成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复合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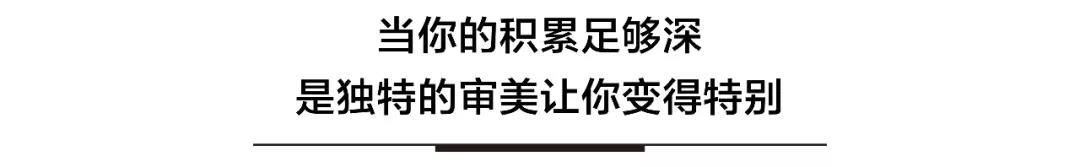
王珞丹 如果没有数字化,你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建筑出来?
袁烽 没有数字化也一样做。
王珞丹 那你等于失去了“手臂”,你的思维就没有办法延展了。
袁烽 有工具以后,我觉得自己已经跟工具融为一体了,可能我在构思的时候也没有刻意想那些机器人,但是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潜意识里知道我能做到什么。这里面的很多东西是原来的建筑师很少接触到的,认为这是做土木工程和做测量的人员的专业领域,不是做艺术设计的人该关注的。我们现在是高度集成,只要觉得有用我都会拿来研究。
王珞丹 那你现在你怎么区分艺术和技术?
袁烽 好像也没有特别刻意区分它,也不能刻意区分。艺术的东西我觉得是天生的,它是“植入”的,它就在那,但是一个工作室里面也不能都是太艺术的人。
王珞丹 那你是不是两者兼备?
袁烽 我是切换频道比较快的,这两个频道可以无缝切换。
王珞丹 有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或在某一个事件上,两者会打架?需要去平衡吗?
袁烽 一直在平衡,每时每刻每一个会议都是在平衡这个关系。我之前说艺术是“植入”的,意思是我们从小成长的经历和受到的建筑学教育背景,会影响我们的很多判断。而且一个人不管你的审美如何,都是一种特性。我的学生常和我说,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自己总觉得丑,我也会去鼓励,“这是你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当你的其他东西积累到一定程度,你独特的审美会让你变得很特别。因为很多时候丑和美其实就隔了一层纱而已,一旦跨过去就有美的意义了,当代艺术也是一样。


王珞丹 当代艺术是不是对您做建筑的表达也有很大的影响?
袁烽 很有影响。很多人问我,我是做什么风格的,我是受什么影响;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的建筑师应该做现代的事情,就是有“当代性”,而这种当代性不是从某一个人那学来的,因为当代性就是当下,是当下这个瞬间,那几万分之一秒就是当代,就是此刻很多东西的集成。它的真实性很重要,这个刹那如果是虚假的——比如这个刹那你去学了某个大师在50年以前做的事情、把它复制到现在——那么虽然可能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品,但你的复制已使它失去了意义。即使你学的有7分相似,再有3分“意化”,我都觉得意义不大。我觉得在当下就要用现代的审美,现在的技术,去创造一个现代的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你们做演员做艺术家,可能也一样吧,用别人的范式演得很像了,那又怎么样呢?对吧。
王珞丹 “疑似某人”。
袁烽 对。表演的训练当中可能会教一些范式,包括他人的手势,出场方式,谈话方式,这些都可以被教的,但可以被教的东西都不是最当代的东西——当代的事情是被创造的。创造即有一种独特性,包括一种个体化的创造性,是很有意思的。

王珞丹 但是如果只讨论“当代”的话,建筑本身是一个可能我们都不在了它还在的东西,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去考验,所以这两者之间你觉得应该怎么去平衡?
袁烽 我们建筑学里的专业词叫“自主”,建筑是具有自主性的一个学科。所谓的自主性就是它既有向内的一面,比如说我的建筑所解决的一个问题——它可以剥离于社会、人和其他一切;还有就是外在的一面。建筑的好坏是要在后面更长的时间段内来评价的,像这个房子盖了十年了,用十年来审视一个房子是怎么一个概念。有一些盖了第一年觉得挺好,再隔了几年,我自己也不愿意去了。
王珞丹 好想知道是哪一个(笑)。
袁烽 这种情况早期会有,现在不太会了。像四川崇州那个竹里,我每次去、每个季节去感受都不一样。我们在门口规划了一个菜地种大白菜,那个白菜长的真好,从白菜青葱视角去看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感觉;隔一段旁边的油菜花开了,又是油菜花的感觉——房子是活的。就是我自己,也会很喜欢自己做的这个房子。


又像这个五维茶室,尽管我平时工作不在这,但是我见朋友,开一些会议,谈事情都在这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交流空间,而且使用的频率很高,也还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虽然茶室是一个临时改造,没有任何奢华的材料,没有大理石,没有很贵的墙纸,每一件是都是最朴素的,但我也用了十年了。我仍然觉得这个房子很亲切,它对我来说有特别的个性——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最珍贵的,不同建筑师都会找到属于他的那块东西。


王珞丹 我其实很好奇,您都是用机器、电脑、数字化技术做出来的建筑,机器本身是冰凉的,但是一个空间能够留住人、让大家愿意一直再去,包括您说的竹里,一定是有一定温度的。这个温度是什么呢?
袁烽 我觉得这个温度是,我和机器已经分不出彼此了。我现在对机器的看法已经不是机器了,它就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们合作之后一起做一件事情,是这样一种态度。所以那个温度最终还是跟人的人性有关的,当然现在的人性是受到了很多机器性的影响,或者是辅助,或者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人在支配机器的同时机器也在支配人,这是机器特有的工作方式——人有时候也需要顺着机器的思路走,去跟它合作,就跟俩人过日子一样,相互之间需要一种适应。
王珞丹 那有点像夫妻关系似的,是不有那么一瞬间你会被它牵制住了?
袁烽 也有这种可能性,但与人不同的是,机器的迭代非常之强。它有一个好处是可以24小时不停地工作。
王珞丹 工作狂。
袁烽 而且人的双手是有极限的。比如说普通人单手提起30公斤并且能连续重复一个动作,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机器可以一边提125公斤,另一边也是125公斤,而且双侧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人想要同时做两件事是很难的,需要训练;而机器只需要编好程序就可以了。
王珞丹 那会不会,这么多年跟机器相处下来,会发觉跟人打交道反而更累一点?
袁烽 有一点。中国人是很复杂的一个民族,中国的人情,交流,都是很复杂的。
王珞丹 人是有变化的,人也会情绪不稳定。
袁烽 不过对我来说,人有人的脾气,机器有机器的脾气,相处当中都还是要大家相互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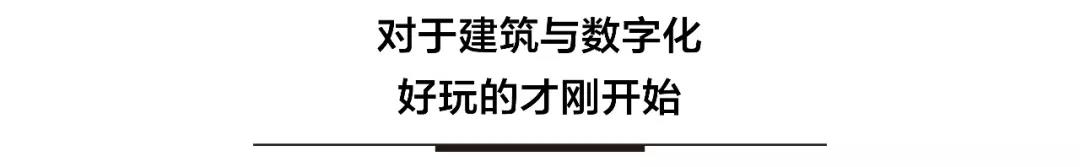
王珞丹 您会期待完全不需要人做建筑的时候到来吗?
袁烽 没有,现在是人机协作的阶段。我觉得从大环境来看,我们这一代人活着的时候,还是人机协作的大时代。我们今年夏令营的主题叫赛博未来(Cyborg Futures),就像很多科幻小说、电影里出现的一样,人会在头上戴一些设备,甚至是半人半机器,这就是赛博人。我们这代人很有可能看到赛博未来,只不过不是像科幻片里机器长在你身体上,而更可能是在体外的一种赛博。比方说一个手机是一个赛博,一辆汽车也是,一个飞机也是,你已受到周围很多机器的左右,只不过你还没意识到。如果有一天把你放到很远的地方,没有手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一个人在大自然中,你才会发觉你自己和那个原始时代,已经产生了一种差异。
王珞丹 我现在也不行,丢了手机我就会觉得今天空落落的。不过不说别的,就说建筑,现在这种数字化的发展,让我看到了很多在以前的建筑上看不到的形态。
袁烽 还有好多没有做出来呢,后面还会有更多的出来。数字化才刚刚开始。我觉得很多人很悲观,不管是对建筑还是对数字化,我还是蛮乐观的,好玩的才刚开始,现在我们所实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王珞丹 百分之多少?
袁烽 一点点,真的,目前只是很少一点。因为能熟练操作这些机器人的人,现在全世界也就这么多,这个需要更多人来做—— 一个人做或是一个团队做,在思维上还是有很大限制。

……
版权声明:本文资料由王珞丹工作室、创盟国际提供,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欢迎转发,禁止以有方编辑版本转载。
投稿邮箱:media@archiposition.com








